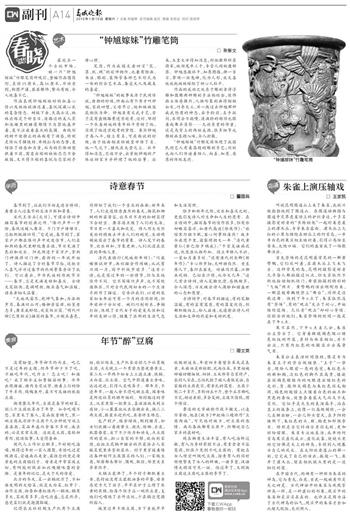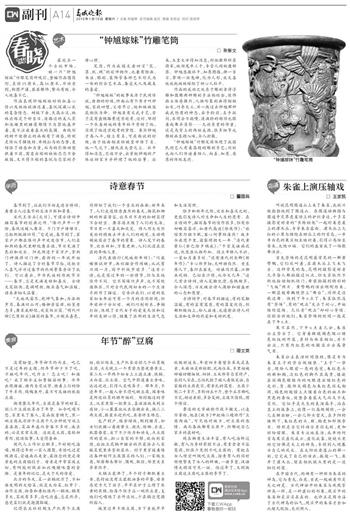□ 周文英 没有盼望,年节却不约而至。吃已不是过年的主题,但年节却少不了吃。不缺吃年代,吃什么?怎么吃?和谁吃?成了颇令主妇费脑筋的事。今年出现猪瘟,猪肉自觉让贤,抢着上位的除了牛羊肉、鸡鸭鱼外,最不可或缺的就数豆腐。 物质匮乏年代,豆腐是春节的好菜,割二斤豆腐就算办了年货。如今吃喝不愁,家里来了客人,菜品数量稍欠,煎一碗豆腐或凉拌个豆腐干几分钟就可端上桌凑数,菜品丰盛而食客不多时,减去的,必是家常豆腐。这就是豆腐,柔软却有形,能顶住事,又受得委曲。 现代人工作忙应酬多,平时胡吃海喝,难得过年时一家人团聚,奇怪吃过星级酒店,尝遍南北美食,最挂念的竟是母亲包的豆腐馅饺子。母亲是平常家庭主妇,有何能耐做出如此唤醒味蕾的食物。是童年的记忆,是大于天的母爱。 北方的冬天,菜一出锅就凉了,不知谁发明的大烩菜,就是大白菜、红萝卜、油炸豆腐、粉条和着红烧肉一锅炖,锅有多大,菜就有多多,边吃边盛,总是热乎,感觉菜们就是抱团取暖。 记得农业社时期生产队有个豆腐坊,秋忙结束,生产队长安排几个社员做豆腐,头天晚上一个男劳力整夜磨黄豆,第二天一早两个妇女上工滤豆渣、烧锅、点白浆、压豆腐。空气中弥漫着豆香味,远远近近,引得人直吸鼻子。那年月,不逢年节,一般人舍不得吃顿豆腐,闻香味是附近社员的额外福利。邻村路过的学生,从家里偷一把黄豆,喜滋滋地来到豆腐坊,小心翼翼地从衣袋掏出来,换二三两豆腐,蘸浆水趁热吃,其香终生难忘。 包产到户,粮食增收,刚到腊月,妇女们就操心着拣黄豆、淘洗、晾晒、去皮,机器磨浆,省下不少体力和功夫,点豆腐用的浆水,担心自家的不够,就向别家借,后把豆花锅中撇出的热浆添去人家酸菜瓮里再育新浆水。村子里穿梭着借还各种制作豆腐器具的人们,一家做豆腐,邻居都来帮忙、围观、取经,邻里关系异常热乎。 大锅豆浆沸了,半个村子都飘着豆香,农村娃没有豆浆配油条的早餐,母亲感觉亏欠了孩子,早早在炉子上烤了焦黄的蒸馍,给每个孩子舀一碗热豆浆,支他们吃喝饱了去外边玩,少在锅边踅摸绊搭人。 城里过年不做豆腐,乡下亲戚早早就做好送来,年前回乡看望长辈或是表亲,米面油是新标配,礼尚往来,乡里姑姨婶娘回赠核桃、柿饼、玉米糁等自家特产,农村人实在,总怕礼轻了被人看低笑话,自家做的豆腐瓷实,有重礼的寓意。豆腐少则二十多斤,多则四五十斤,整个正月都吃不完,转送亲朋,多会笑纳,豆腐不值钱,图个情谊。 鲁迅的文章被称作战斗檄文,以凌厉著称,他在《故乡》中把杨二嫂称作“豆腐西施”,可见他对故乡,对豆腐的感情。南北各地都有豆腐干,但都说自己家乡的最好吃。 现在物质生活丰富,有人吃海鲜过敏,有人为身材荤腥不沾,有素食者不容葱蒜,但很少见到不吃豆腐的。有把占女人便宜叫做吃豆腐,指责男人的同时顺便赞美了女人的鲜嫩,一语多意,汉语博大精深可见一斑。快过年了,又到做豆腐送豆腐吃豆腐的季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