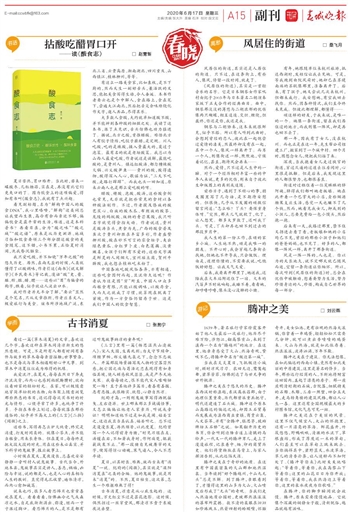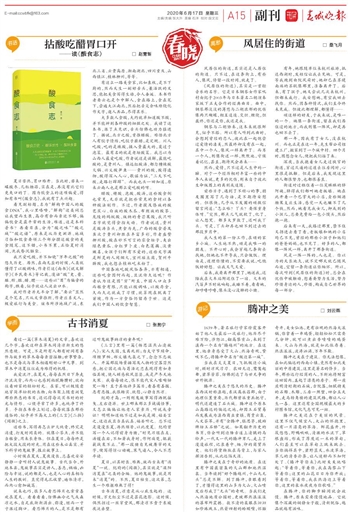□ 张渤宁 看过一篇《草木消夏》的文章,喜欢这几个字,喜欢这种在草木间清凉渐生的悠然意境。可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有条件与故乡的草木每每亲密接触;世事繁杂,也不是每次与草木相遇刚好心中无事。到草木中消夏往往成为难得的机缘。 我爱流汗,在夏天,每每在烈日下奔走汗流浃背,而内心也感到粘腻腌臜时,就向往着回家的轻松时光。在家,可以极随意地穿简单松软的衣物,向书架上随意浏览那些熟悉的书目,还记得每次买书时的时光与情形。心便寻常了许多,也纯净了许多。手指在书脊上划过,每每就落在那些通俗的、似乎并不高大上的《三言》《二拍》《阅微》之上。 这些书,写得再怎么炉火纯青,终究是消遣、打发时间类的。就像小茶点,并不能当粮食,用来长身体。但在夏日,每每终是把大段大段的时光,用在这些未必真实、并不科学的鬼故事、报应故事上。 小时候在夏天,夏夜漫长,总喜欢安安静静一旁听村人说鬼故事。古代当今,外地本县,鬼故事其实是讲人,善恶,祸福,凶险与幸运,说的都是人,也是人心的真相与人生的教训。直觉得毛孔收紧,遍体清凉,而内心愈加诚笃。 说来也巧,很多人看恐怖片也常常喜欢在夏天。看着看着,仿佛幽冷之气或森凉之水,自足底渐渐涌出、弥漫,继而一寸寸涨过胸口。看恐怖片的人,是不是都有过听鬼故事纳凉的童年呢? 《三言》里有一篇《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宋人失国,生离死别;为夫守节殒命,项缠罗帕,郑义娘九泉之下,念念不忘故人。开篇那段场景描写及人物的空落茫然感,把亡国之痛与苟活之悲表现得有如身临其境,使人顿感秋风瑟瑟,或是严冬天地大寒。我每每读之,恨不能代宋人嚎啕恸哭一场!至于其他许多篇目,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很踏实、欣慰,心静自然凉。 纪昀才高,一则则鬼故事写得洒脱摇曳、左右逢源。世上哪来那么多诡谲怪事,又怎么偏偏让他老人家亲历、听说或旁证?明明知道他不过是如我是闻、姑妄言之,这边我且当真认真、姑妄听之。总不过是漫漫长夏,溽热烦苦,以此度夏。纪昀曾写一个人记得前身为猪,“时见刀俎在左,汤镬在右,不知著我身时,作何痛楚,辄簌簌战栗不止。”那一段猪自见被屠宰的文字,便写得惊心动魄,寒气逼人,令人不忍卒读。 夏日,以其时长、难熬,故而古来有“消夏”一说。纪昀的《阅微》,其实就是“滦阳消夏录”之类的合编。他的鬼故事,就是用来“消夏”的。不然,夏日枯坐,这次第,怎生一个难捱难熬了得! 古书消夏,凉意是从心底生起的。这时候,万丈红尘不过是昙花泡影。这时候,偶然掠过一丝穿堂风,那清凉不啻于东坡夜泛赤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