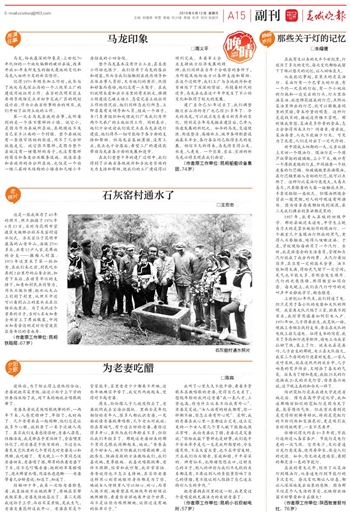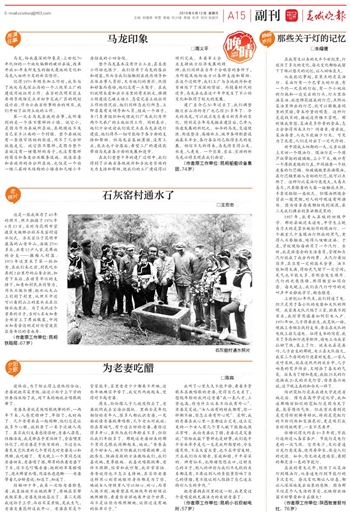□朱耀儒 在我有生以来的大半个世纪里,灯经历了多次的变化,每次变化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让人回味良久。 从我能记事起,家里点的是菜油灯。菜油灯有一个巴掌大的灯座,有一个约一尺长的灯柱,有一个小碗状的灯拖和一边突出的灯头,灯头里添满菜油,放进棉花搓成的灯芯,点燃从菜油里伸出的灯芯,就可以驱散房间里的黑暗,带来珍贵的明亮。这种灯是花钱买的,据说还价格不菲呢。那时候我常想,菜油是多珍贵的食品,怎么会舍得用来点灯?问母亲,母亲说,菜油再贵,人也不能缺少灯光。可见为了光亮,人们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天,父亲从镇上买回一个煤油灯。煤油灯是一个葫芦状带把的玻璃瓶,上小下大,瓶口有一个薄铁皮做的灯盖,中间插着一个铁皮卷的灯芯桶。给玻璃瓶里添满煤油,在灯芯桶里插入自制的灯芯,就可以点燃了。这种灯比菜油灯亮度大,又易点易灭,只要擦着的火柴一接触就点燃,手靠近轻轻一扇就灭。但煤油燃烧会冒出一股黑烟,对人的呼吸道有所损伤。因为母亲每夜都纺线到深夜,第二天我们擤出的鼻涕都是黑的。 1957年,我考入县城的初级中学。那时县城还未通电,中学生上晚自习点的是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一个教室几十盏煤油灯燃放的黑气,熏得人头昏脑涨,呛得人咳嗽流涕。于是,学校便给每班买了一个汽灯。当时,我是班委会的生活委员,管理和点汽灯就成了我分内的事。点汽灯看似简单,其实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油不能加得太满,得给充气留下一定空间;充气也不能太多,否则会发生爆炸。汽灯的光亮很强,照得教室如同白昼。每天晚上,我们在汽灯呼呼的欢叫声中安静地学习,颇感惬意。 上世纪60年代末,我们村通了电。但只是用于各小队的电磨和大队的照明。我家离大队只隔了三家,距离不到百米,我经常思谋着如何引电入户。1970年初,儿子将要出生,我灵机一动,便揣上香烟去找村支书,要求在大队的电线上挂火通电。征得支书的同意,我买了导线和灯泡等配件,请电工为我家拉好了线,装上了灯。说来也真是凑巧,儿子出生的那晚,电工在大队挂火,我家三个房间的灯泡霎时发亮,一家人欢呼雀跃,就在这热烈的欢乐中,儿子响亮的哭声传出,又增添了喜庆的气氛。后来为了增加亮度,我把25瓦的灯泡换成20瓦的日光灯管,母亲高兴地说,这下晚上真的和白天一样了。 结识霓虹灯是在我读大学走进省城之后。因为在高中学过化学,我知道那绚丽灿烂的霓虹灯是因为充了氦、氖等惰性气体。但我首次看到还是觉得特别稀奇好玩,特别是霓虹灯的不断闪烁和变换色彩,更是吸引我长时间地观赏,一直不忍离开。 依稀记得大约在10多年前,节能灯逐渐进入各家各户。节能灯是电灯史的一次飞跃。它用电少,又比普通日光灯亮度高,使用寿命长,很受人们的欢迎。如今,你无论走进谁家,看到的都是清一色的节能灯。 在我的有生之年,经历了从菜油灯到煤油灯,从普通电灯到节能灯的多次变化。每次变化都让人惊喜,都让人深深地发出由衷的感慨。因为那不仅是个人生活的享受,也映射出祖国不断繁荣和日益强大! (作者原工作单位:陕西教育报刊社, 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