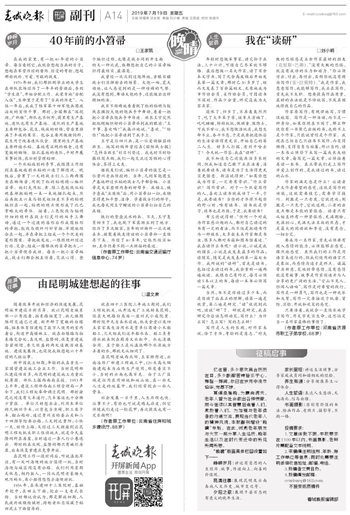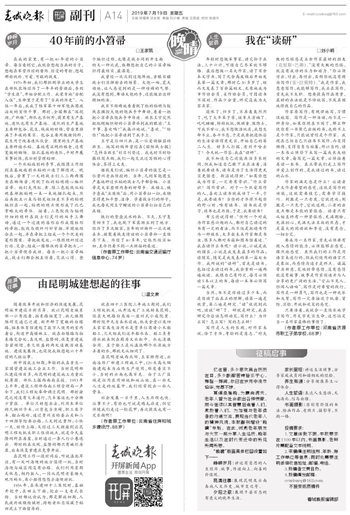□王家凯 在我的家里,有一把40年前的小笤帚。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当兵的日子,想起在军营历经的磨炼、经受的考验,想起那些纯朴、可爱、可敬的战友。 1970年初,我们那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在部队农场经历了一年半的劳动后,告别“学生连”,开始分配工作。我荣幸地“分配入伍”,生命里于是有了“当兵的历史”。入伍一年后,我成了陆军第十四军炮兵团政治处的宣传干事。那时,全国都在“深挖洞,广积粮”,部队也不例外,团里有生产基地,连队也有生产基地。连队的生产基地主要种包谷、花生,秋收的时候,营房里挂满了丰收的果实。包谷主要用做猪饲料,花生用于改善连队伙食。团里的生产基地主要种植水稻。基地有正规的粮仓,还有宽敞的晒场。驻扎基地的连队,平时开展军事训练,农忙时管理稻田。 一个水稻收割的季节,我随团工作组到在基地收割水稻的六连了解情况。晚饭后,劳累了一天的战士们三三两两围坐在晒场旁,用脱了粒的稻穗精心编织笤帚。他们先用红、黄、绿三色胶线从稻穗基部把稻穗一束一束地捆扎起来,然后再把五六束与铅笔粗细差不多的稻穗编织在一起,稻穗的穗头便形成了比巴掌略大的帚体。接着,三色胶线与稻穗纤细的穗秆在战士们灵巧的双手上舞动,通过一个过渡的扇形后形成圆柱形的帚把,胶线与穗秆巧妙穿插,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帚把上组成一个个优美的菱形图案。帚把收尾处,一根根穗秆经过打结、交会,组成一圆锥状的笤帚把头,一把小笤帚便告成功。每当一把小笤帚编成,战士们都会相互传看,交流心得。整个编织过程,也像是战士间别开生面的又一种比武,谁都想把自己的小笤帚编织得最结实、最漂亮。 我曾经一次次到过炮阵地,亲眼目睹战士们实弹射击的场景。大炮一响,震天动地,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磅礴的气势。我没有想到,舞动大炮的手,还能做出这样精细的活。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脱了粒的稻穗与胶线在操控大炮的炮兵手中舞动,看着一把把小笤帚在炮兵手中传递。班长王宁突然把他刚编织好的小笤帚举到我的眼前:“王干事,喜欢吗?”我高兴地说:“喜欢。”“给你!”他把小笤帚递到了我手上。 王宁是位四川兵,是一位爱动脑筋的班长。他写的稿件曾经在《国防战士报》“怎样当班长”栏目刊登过。我也时不时给报社写点稿,我们一起交流过写稿的心得体会,算得上文友。 据战友们说,编织小笤帚的技艺是一位贵州老兵传授的。当年,凡到军炮团生产基地种过水稻的战士几乎都会编。小笤帚是大家整理内务的好帮手。床铺上,被子叠成“豆腐块”后,用小笤帚扫一扫,床铺显得更加平整、洁净。学着战士们的样子,我也每天用王宁赠送的小笤帚打扫自己的床铺。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久,王宁复员回乡了,我也脱下军装转业到了地方。经历了多次搬家,当年的旧物件一次次被丢弃,凝聚着战友情谊的小笤帚却一直保存下来。历经了40多年,它依然结实如初,至今仍看不到一点拼接的痕迹。 (作者原工作单位: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信息中心,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