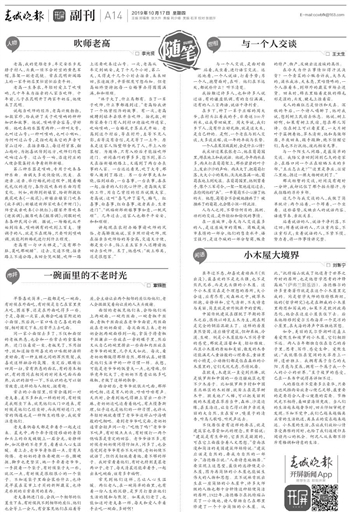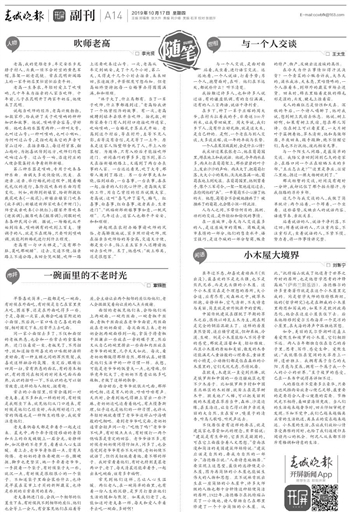□ 李光贤 老高,我的楚雄老乡,牟定安乐乡龙脖子村人,头戴一顶不合时宜的黄色军帽,鼻架一副老花镜。常在昆明新闻路上的一家牛奶店里忙前忙后卖牛奶。 老高一生务农,年轻时爱上了吹唢呐,几十年来为接亲的人家当吹师。十年前,儿子在昆明开了两家牛奶店,他便来了昆明。 说起当吹师的经历,老高兴致勃勃,如数家珍,给我讲了关于吹唢呐的种种知识和故事。他说,唢呐学会容易,学好难。他吹奏的乐器有两种:一种叫大号,也叫过山号;一种叫唢呐,也叫小喇叭。为何叫过山号,是指吹起来它的声音可穿山过岭。在接亲路上,每过村穿寨,翻山越岭,为把喜讯传到远方,吹师们均需吹响过山号。过山号一响,沿途村庄的人便会聚集村头争看新郎新娘。 第二种乐器是唢呐,专用于吹奏各种乐曲。曲调大多欢快愉悦、优美。在迎亲、送亲、举行婚礼的过程中,随着婚礼礼仪的进行,各阶段吹奏的乐曲均有变化。例如,新郎到新娘家,给新郎披红戴花吹奏《一枝花》;新娘出娘家门吹奏《放羊调》;新娘进新郎家吹奏《开财门》;拜堂成亲吹奏《小桃红》;摆宴开席吹奏《迎宾调》;撤席吹奏《撤席调》;闲暇时吹奏各种民间小调。据说,一场婚礼从开始到结束,唢呐调有的吹到上百支。懂调子的人,就是不在现场,只要听到唢呐调,就能判断婚礼进行到什么程度。 老高有一句口头禅是,“没有那个肚,莫吃那碗醋”。过去,交通不便,接亲路上不通公路,来回全凭双腿,吹师一路上还要吹奏过山号。一次,老高从牟定到姚安,走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又得走十几个小时去接亲,来来回回,长途跋涉,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但老高始终坚持把每一台婚事办得圆圆满满,和和顺顺。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当了一辈子吹师,什么事都遇到过。”老高给我讲了一个他曾经历的故事。有一次,老高被聘到禄丰县琅井当吹师。按礼数,新郎家要专门有人到村口迎接吹师进家,吹响唢呐,一台婚礼才算正式开始。老高到这个村后,等在村外,左等不见人影,右等没有音信,足足等了一上午。原来是这家人隔壁邻舍死了人,早上入殓装棺。为避讳,只有入殓后才能接吹师进门。世间凑巧的事多多,想不到,第二天在接新娘的路上,又遇到了两台办丧事的人家。一台远远看见,吹了大号,那帮人避到了路边。另一台却事先未知晓,临到碰面,一台喜事,一台丧事,凑在一起,接亲的人们忧心忡忡,老高做大家的工作,用自己曾经的经历说服大家。老高说:这叫“喜气冲了霉气、晦气。红喜事,白喜事,红白喜事,逝者离去,生者进门”。“祝福新郎新娘事事如意,一帆风顺”。几年过去,这家人也都平平安安,和和顺顺。 讲起现在农村办婚事请吹师的风俗,老高骄傲地说,家乡照旧请吹师,现在接亲当吹师给的筹金高,交通又方便,都是坐小车,隔三差五家乡人还聘请他回去当吹师。末了,他感叹:“故土难离,还是很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