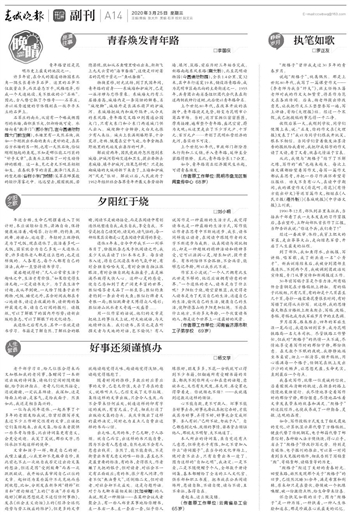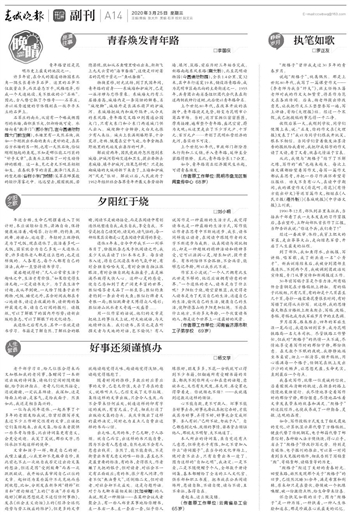□杨文学 老干部学习日,给几位很合得来而又知根知底的老同事,各赠阅了一本新近出版的诗词集,请他们空闲时随便翻翻,给予批评指正。老哥儿们欣然接受,还说谢谢,一定认真拜读。我深知,这是场面上的话,是客气,是给我面子。然虽如此,我还是相当高兴的。 一位与我同年退休、一起共事了十多年的老朋友给我说,你曾经撰写并发表过不少工作研究性质的文章,应该把它们集结起来,出成文集,给后来者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比出诗词集更有意义,会更受欢迎。我笑了笑说,那些文字,恐怕承担不起这样的使命。 文章和孩子一样,都是自己的好。我嘴上谦虚,心底里却不免敝帚自珍,虽此前也不止一次地自我否定过出论文集的想法,但还是因“受到鼓舞”而再一次跃跃欲试。我开始认真审阅自己以往的文章。起初还为某些篇什不乏见地而感到欣慰,比如,分别发在新华网“精粹”栏目和“理论频道”上的《“否决”并非越多越好》《解放思想就是不迷信任何事物》,发在《社会主义论坛》上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劳工权益的维护》,但更多的文章就越读越觉得乏味,越读越觉得浅陋,越读越觉得尴尬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数应时应景应事的文章,已毫无价值,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说难听点儿,已经变成了文字垃圾。集结这样的文章出版,只会令人生厌,而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制造这样的印有字迹的废纸,有害无益,于是,彻底打消了出版论文集的念头。我庆幸做出了这样的最终决定,同时也为差点儿自费出这样的书而心惊。 出乏味、无用的书,于己无聊,于人添烦。就自己而言,出这样的书只能自费,因为不会有人愿意读,自然也就不会有人愿意出钱买。当然了,能不能卖钱,不是衡量出书有无意义的唯一标准,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标准,有的书,卖得很火,作者赚了大把的银子,但对读者、对社会不一定有正面效应;有的书,很少有人问津,作者不仅“熬油费火”,还倒贴二文,但对读者、对社会却不乏益处。这是句题外话。对于与无聊书籍相关联(比如受赠)的人来说,则是一种烦恼——在某种会议或者聚会上,有一些人郑重其事地给你赠书,左一本右一本,左一套右一套,似乎你人缘很好,朋友多多,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得到不少书籍,但翻遍所有受赠书籍的目录,都找不到你所关心和在意的话题,意欲弃之,又恐有失风度,再无用、再受累也得带着走。你说烦也不烦?——我就遇到过数次这样的烦恼。 心不能自欺,更不可欺人。坏事不能当好事去办,好事也要认真把它办好,才能成其为好事,弄得不好,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圣人有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都感到乏味、厌烦的事情,若再拿去烦恼他人,那就太不明智、太不地道了。 本人所出的诗词集,虽自觉还有点儿意思,但毕竟水平有限,加之不曾加入什么“诗词圈子”,在当今的文化市场上,绝对卖不出去,只有自费出书一途了。因为这样的“自知之明”,我决定:一是不卖,二是不随便赠予个人,全部数千册诗词集,基本都赠给了全省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和职工书屋。把书放在公共阅读场所,愿读自取,不读自便,读与不读,互不牵扯,各得自在。 看起来,这么做没错。 (作者原工作单位:云南省总工会 6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