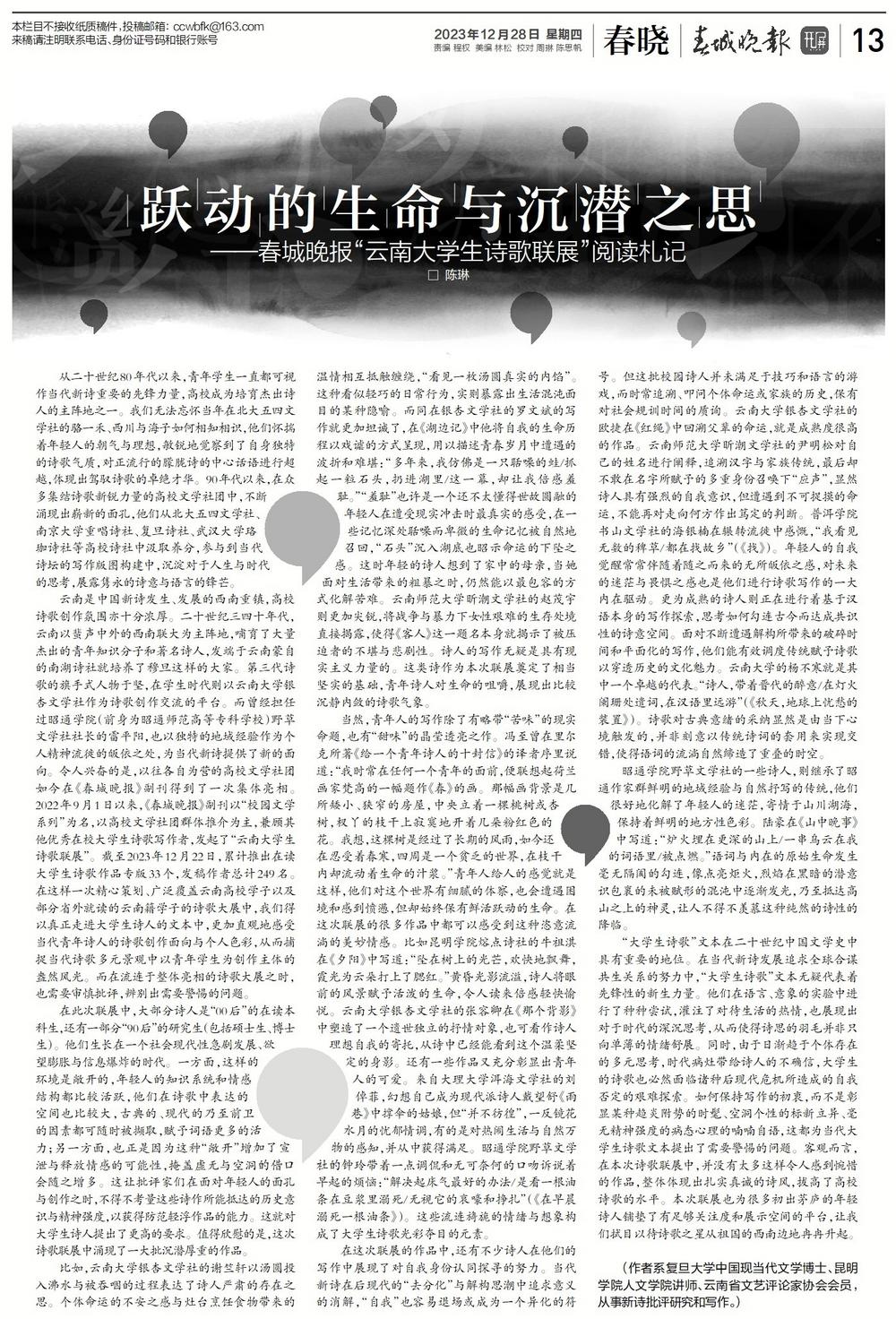□ 陈琳
从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青年学生一直都可视作当代新诗重要的先锋力量,高校成为培育杰出诗人的主阵地之一。我们无法忘怀当年在北大五四文学社的骆一禾、西川与海子如何相知相识,他们怀揣着年轻人的朝气与理想,敏锐地觉察到了自身独特的诗歌气质,对正流行的朦胧诗的中心话语进行超越,体现出驾驭诗歌的卓绝才华。90年代以来,在众多集结诗歌新锐力量的高校文学社团中,不断涌现出崭新的面孔,他们从北大五四文学社、南京大学重唱诗社、复旦诗社、武汉大学珞珈诗社等高校诗社中汲取养分,参与到当代诗坛的写作版图构建中,沉淀对于人生与时代的思考,展露隽永的诗意与语言的锋芒。
云南是中国新诗发生、发展的西南重镇,高校诗歌创作氛围亦十分浓厚。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以蜚声中外的西南联大为主阵地,哺育了大量杰出的青年知识分子和著名诗人,发端于云南蒙自的南湖诗社就培养了穆旦这样的大家。第三代诗歌的旗手式人物于坚,在学生时代则以云南大学银杏文学社作为诗歌创作交流的平台。而曾经担任过昭通学院(前身为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野草文学社社长的雷平阳,也以独特的地域经验作为个人精神流徙的皈依之处,为当代新诗提供了新的面向。令人兴奋的是,以往各自为营的高校文学社团如今在《春城晚报》副刊得到了一次集体亮相。2022年9月1日以来,《春城晚报》副刊以“校园文学系列”为名,以高校文学社团群体推介为主,兼顾其他优秀在校大学生诗歌写作者,发起了“云南大学生诗歌联展”。截至2023年12月22日,累计推出在读大学生诗歌作品专版33个,发稿作者总计249名。在这样一次精心策划、广泛覆盖云南高校学子以及部分省外就读的云南籍学子的诗歌大展中,我们得以真正走进大学生诗人的文本中,更加直观地感受当代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面向与个人色彩,从而捕捉当代诗歌多元景观中以青年学生为创作主体的盎然风光。而在流连于整体亮相的诗歌大展之时,也需要审慎批评,辨别出需要警惕的问题。
在此次联展中,大部分诗人是“00后”的在读本科生,还有一部分“90后”的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他们生长在一个社会现代性急剧发展、欲望膨胀与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面,这样的环境是敞开的,年轻人的知识系统和情感结构都比较活跃,他们在诗歌中表达的空间也比较大,古典的、现代的乃至前卫的因素都可随时被撷取,赋予词语更多的活力;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种“敞开”增加了宣泄与释放情感的可能性,掩盖虚无与空洞的借口会随之增多。这让批评家们在面对年轻人的面孔与创作之时,不得不考量这些诗作所能抵达的历史意识与精神强度,以获得防范轻浮作品的能力。这就对大学生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值得欣慰的是,这次诗歌联展中涌现了一大批沉潜厚重的作品。
比如,云南大学银杏文学社的谢竺轩以汤圆投入沸水与被吞咽的过程表达了诗人严肃的存在之思。个体命运的不安之感与灶台烹饪食物带来的温情相互抵触缠绕,“看见一枚汤圆真实的内馅”。这种看似轻巧的日常行为,实则暴露出生活混沌面目的某种隐喻。而同在银杏文学社的罗文斌的写作就更加坦诚了,在《湖边记》中他将自我的生命历程以戏谑的方式呈现,用以描述青春岁月中遭遇的波折和难堪:“多年来,我仿佛是一只聒噪的蛙/抓起一粒石头,扔进湖里/这一幕,却让我倍感羞耻。”“羞耻”也许是一个还不太懂得世故圆融的年轻人在遭受现实冲击时最真实的感受,在一些记忆深处聒噪而卑微的生命记忆被自然地召回,“石头”沉入湖底也昭示命运的下坠之感。这时年轻的诗人想到了家中的母亲,当她面对生活带来的粗暴之时,仍然能以最包容的方式化解苦难。云南师范大学昕潮文学社的赵茂宇则更加尖锐,将战争与暴力下女性艰难的生存处境直接揭露,使得《客人》这一题名本身就揭示了被压迫者的不堪与悲剧性。诗人的写作无疑是具有现实主义力量的。这类诗作为本次联展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青年诗人对生命的咀嚼,展现出比较沉静内敛的诗歌气象。
当然,青年人的写作除了有略带“苦味”的现实命题,也有“甜味”的晶莹透亮之作。冯至曾在里尔克所著《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译者序里说道:“我时常在任何一个青年的面前,便联想起荷兰画家梵高的一幅题作《春》的画。那幅画背景是几所矮小、狭窄的房屋,中央立着一棵桃树或杏树,杈丫的枝干上寂寞地开着几朵粉红色的花。我想,这棵树是经过了长期的风雨,如今还在忍受着春寒,四周是一个贫乏的世界,在枝干内却流动着生命的汁浆。”青年人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他们对这个世界有细腻的体察,也会遭遇困境和感到愤懑,但却始终保有鲜活跃动的生命。在这次联展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恣意流淌的美妙情感。比如昆明学院熔点诗社的牛祖淇在《夕阳》中写道:“坠在树上的光芒,欢快地飘舞,霞光为云朵打上了腮红。”黄昏光影流溢,诗人将眼前的风景赋予活泼的生命,令人读来倍感轻快愉悦。云南大学银杏文学社的张容卿在《那个背影》中塑造了一个遗世独立的抒情对象,也可看作诗人理想自我的寄托,从诗中已经能看到这个温柔坚定的身影。还有一些作品又充分彰显出青年人的可爱。来自大理大学洱海文学社的刘倬菲,幻想自己成为现代派诗人戴望舒《雨巷》中撑伞的姑娘,但“并不彷徨”,一反镜花水月的忧郁情调,有的是对热闹生活与自然万物的感知,并从中获得满足。昭通学院野草文学社的钟玲带着一点调侃和无可奈何的口吻诉说着早起的烦恼:“解决起床气最好的办法/是看一根油条在豆浆里溺死/无视它的哀嚎和挣扎”(《在早晨溺死一根油条》)。这些流连旖旎的情绪与想象构成了大学生诗歌光彩夺目的元素。
在这次联展的作品中,还有不少诗人在他们的写作中展现了对自我身份认同探寻的努力。当代新诗在后现代的“去分化”与解构思潮中追求意义的消解,“自我”也容易退场或成为一个异化的符号。但这批校园诗人并未满足于技巧和语言的游戏,而时常追溯、叩问个体命运或家族的历史,保有对社会规训时间的质询。云南大学银杏文学社的欧捷在《红绳》中回溯父辈的命运,就是成熟度很高的作品。云南师范大学昕潮文学社的尹明松对自己的姓名进行阐释,追溯汉字与家族传统,最后却不敢在名字所赋予的多重身份召唤下“应声”,显然诗人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遭遇到不可捉摸的命运,不能再对走向何方作出笃定的判断。普洱学院书山文学社的海银楠在辗转流徙中感慨,“我看见无数的稗草/都在找故乡”(《找》)。年轻人的自我觉醒常常伴随着随之而来的无所皈依之感,对未来的迷茫与畏惧之感也是他们进行诗歌写作的一大内在驱动。更为成熟的诗人则正在进行着基于汉语本身的写作探索,思考如何勾连古今而达成共识性的诗意空间。面对不断遭遇解构所带来的破碎时间和平面化的写作,他们能有效调度传统赋予诗歌以穿透历史的文化魅力。云南大学的杨不寒就是其中一个卓越的代表。“诗人,带着晋代的醉意/在灯火阑珊处遣词,在汉语里远游”(《秋天,地球上忧愁的装置》)。诗歌对古典意绪的采纳显然是由当下心境触发的,并非刻意以传统诗词的套用来实现交错,使得语词的流淌自然缔造了重叠的时空。
昭通学院野草文学社的一些诗人,则继承了昭通作家群鲜明的地域经验与自然抒写的传统,他们很好地化解了年轻人的迷茫,寄情于山川湖海,保持着鲜明的地方性色彩。陆豪在《山中晚事》中写道:“炉火埋在更深的山上/一串乌云在我的词语里/被点燃。”语词与内在的原始生命发生毫无隔阂的勾连,像点亮炬火,烈焰在黑暗的潜意识包裹的未被赋形的混沌中逐渐发光,乃至抵达高山之上的神灵,让人不得不羡慕这种纯然的诗性的降临。
“大学生诗歌”文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当代新诗发展追求全球合谋共生关系的努力中,“大学生诗歌”文本无疑代表着先锋性的新生力量。他们在语言、意象的实验中进行了种种尝试,灌注了对待生活的热情,也展现出对于时代的深沉思考,从而使得诗思的羽毛并非只向单薄的情绪舒展。同时,由于日渐趋于个体存在的多元思考,时代病灶带给诗人的不确信,大学生的诗歌也必然面临诸种后现代危机所造成的自我否定的艰难探索。如何保持写作的初衷,而不是彰显某种趋炎附势的时髦、空洞个性的标新立异、毫无精神强度的病态心理的喃喃自语,这都为当代大学生诗歌文本提出了需要警惕的问题。客观而言,在本次诗歌联展中,并没有太多这样令人感到惋惜的作品,整体体现出扎实真诚的诗风,拔高了高校诗歌的水平。本次联展也为很多初出茅庐的年轻诗人铺垫了有足够关注度和展示空间的平台,让我们拭目以待诗歌之星从祖国的西南边地冉冉升起。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昆明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从事新诗批评研究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