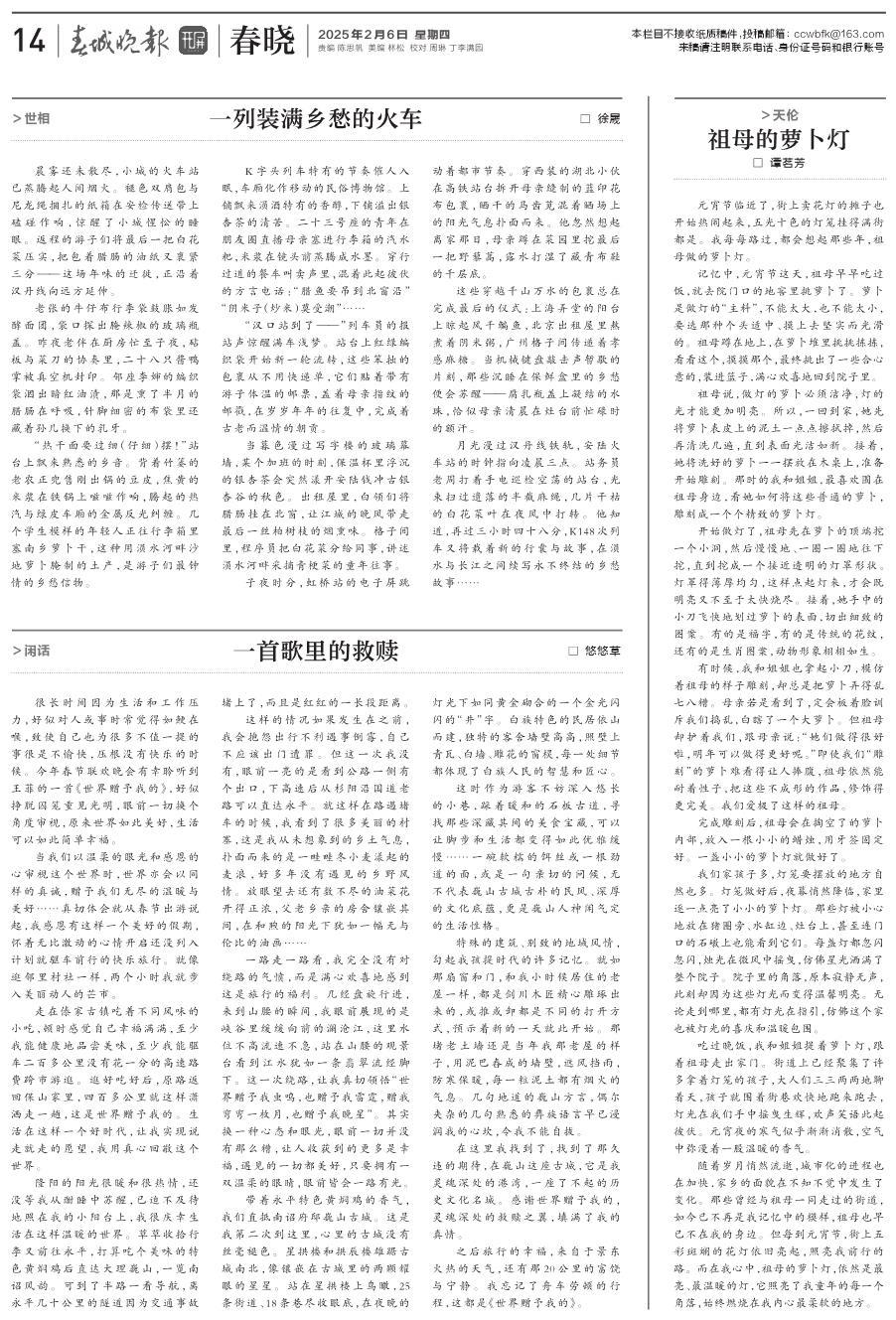□ 徐晟
晨雾还未散尽,小城的火车站已蒸腾起人间烟火。褪色双肩包与尼龙绳捆扎的纸箱在安检传送带上磕碰作响,惊醒了小城惺忪的睡眼。返程的游子们将最后一把白花菜压实,把包着腊肠的油纸又裹紧三分——这场年味的迁徙,正沿着汉丹线向远方延伸。
老张的牛仔布行李袋鼓胀如发酵面团,袋口探出腌辣椒的玻璃瓶盖。昨夜老伴在厨房忙至子夜,砧板与菜刀的协奏里,二十八只酱鸭掌被真空机封印。邻座李婶的编织袋洇出暗红油渍,那是熏了半月的腊肠在呼吸,针脚细密的布袋里还藏着孙儿换下的乳牙。
“热干面要过细(仔细)摆!”站台上飘来熟悉的乡音。背着竹篓的老农正兜售刚出锅的豆皮,焦黄的米浆在铁锅上嗞嗞作响,腾起的热汽与绿皮车厢的金属反光纠缠。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往行李箱里塞南乡萝卜干,这种用涢水河畔沙地萝卜腌制的土产,是游子们最钟情的乡愁信物。
K字头列车特有的节奏催人入眠,车厢化作移动的民俗博物馆。上铺飘来涢酒特有的香醇,下铺溢出银杏茶的清苦。二十三号座的青年在朋友圈直播母亲塞进行李箱的汽水粑,米浆在镜头前蒸腾成水墨。穿行过道的餐车叫卖声里,混着此起彼伏的方言电话:“腊鱼要吊到北窗沿”“阴米子(炒米)莫受潮”……
“汉口站到了——”列车员的报站声惊醒满车浅梦。站台上红绿编织袋开始新一轮流转,这些笨拙的包裹从不用快递单,它们贴着带有游子体温的邮票,盖着母亲指纹的邮戳,在岁岁年年的往复中,完成着古老而温情的朝贡。
当暮色漫过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某个加班的时刻,保温杯里浮沉的银杏茶会突然漾开安陆钱冲古银杏谷的秋色。出租屋里,白领们将腊肠挂在北窗,让江城的晚风带走最后一丝柏树枝的烟熏味。格子间里,程序员把白花菜分给同事,讲述涢水河畔采摘青梗菜的童年往事。
子夜时分,虹桥站的电子屏跳动着都市节奏。穿西装的湖北小伙在高铁站台拆开母亲缝制的蓝印花布包裹,晒干的马齿苋混着晒场上的阳光气息扑面而来。他忽然想起离家那日,母亲蹲在菜园里挖最后一把野藜蒿,露水打湿了藏青布鞋的千层底。
这些穿越千山万水的包裹总在完成最后的仪式:上海弄堂的阳台上晾起风干鳊鱼,北京出租屋里熬煮着阴米粥,广州格子间传递着孝感麻糖。当机械键盘敲击声暂歇的片刻,那些沉睡在保鲜盒里的乡愁便会苏醒——腐乳瓶盖上凝结的水珠,恰似母亲清晨在灶台前忙碌时的额汗。
月光漫过汉丹线铁轨,安陆火车站的时钟指向凌晨三点。站务员老周打着手电巡检空荡的站台,光束扫过遗落的半截麻绳,几片干枯的白花菜叶在夜风中打转。他知道,再过三小时四十八分,K148次列车又将载着新的行囊与故事,在涢水与长江之间续写永不终结的乡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