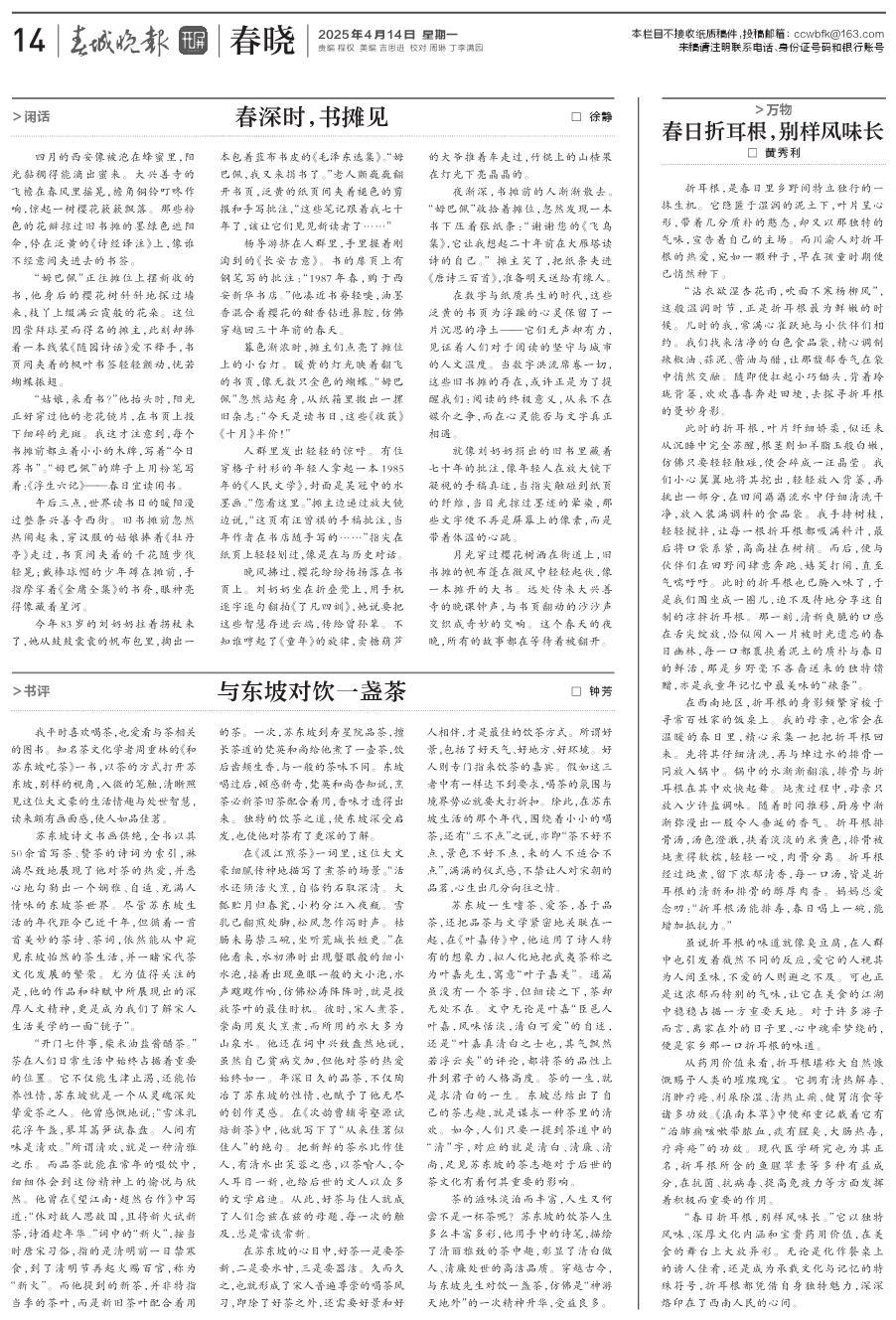□ 钟芳
我平时喜欢喝茶,也爱看与茶相关的图书。知名茶文化学者周重林的《和苏东坡吃茶》一书,以茶的方式打开苏东坡,别样的视角,入微的笔触,清晰照见这位大文豪的生活情趣与处世智慧,读来颇有画面感,使人如品佳茗。
苏东坡诗文书画俱绝,全书以其50余首写茶、赞茶的诗词为索引,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对茶的热爱,并悉心地勾勒出一个娴雅、自适、充满人情味的东坡茶世界。尽管苏东坡生活的年代距今已近千年,但循着一首首美妙的茶诗、茶词,依然能从中窥见东坡怡然的茶生活,并一睹宋代茶文化发展的繁荣。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他的作品和辞赋中所展现出的深厚人文精神,更是成为我们了解宋人生活美学的一面“镜子”。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不仅能生津止渴,还能怡养性情,苏东坡就是一个从灵魂深处挚爱茶之人。他曾感慨地说:“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所谓清欢,就是一种清雅之乐。而品茶就能在常年的啜饮中,细细体会到这份精神上的愉悦与欣然。他曾在《望江南·超然台作》中写道:“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词中的“新火”,按当时唐宋习俗,指的是清明前一日禁寒食,到了清明节再起火赐百官,称为“新火”。而他提到的新茶,并非特指当季的茶叶,而是新旧茶叶配合着用的茶。一次,苏东坡到寿星院品茶,擅长茶道的梵英和尚给他煮了一壶茶,饮后齿颊生香,与一般的茶味不同。东坡喝过后,顿感新奇,梵英和尚告知说,烹茶必新茶旧茶配合着用,香味才透得出来。独特的饮茶之道,使东坡深受启发,也使他对茶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汲江煎茶》一词里,这位大文豪细腻传神地描写了煮茶的场景。“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在他看来,水初沸时出现蟹眼般的细小水泡,接着出现鱼眼一般的大小泡,水声飕飕作响,仿佛松涛阵阵时,就是投放茶叶的最佳时机。彼时,宋人煮茶,崇尚用炭火烹煮,而所用的水大多为山泉水。他还在词中兴致盎然地说,虽然自己贫病交加,但他对茶的热爱始终如一。年深日久的品茶,不仅陶冶了苏东坡的性情,也赋予了他无尽的创作灵感。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中,他就写下了“从来佳茗似佳人”的绝句。把新鲜的茶水比作佳人,有清水出芙蓉之感,以茶喻人,令人耳目一新,也给后世的文人以众多的文学启迪。从此,好茶与佳人就成了人们念兹在兹的母题,每一次的触及,总是常谈常新。
在苏东坡的心目中,好茶一是要茶新,二是要水甘,三是要器洁。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宋人普遍尊崇的喝茶风习,即除了好茶之外,还需要好景和好人相伴,才是最佳的饮茶方式。所谓好景,包括了好天气、好地方、好环境。好人则专门指来饮茶的嘉宾。假如这三者中有一样达不到要求,喝茶的氛围与境界势必就要大打折扣。除此,在苏东坡生活的那个年代,围绕着小小的喝茶,还有“三不点”之说,亦即“茶不好不点,景色不好不点,来的人不适合不点”,满满的仪式感,不禁让人对宋朝的品茗,心生出几分向往之情。
苏东坡一生嗜茶、爱茶,善于品茶,还把品茶与文学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在《叶嘉传》中,他运用了诗人特有的想象力,拟人化地把武夷茶称之为叶嘉先生,寓意“叶子嘉美”。通篇虽没有一个茶字,但细读之下,茶却无处不在。文中无论是叶嘉“臣邑人叶嘉,风味恬淡,清白可爱”的自述,还是“叶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气飘然若浮云矣”的评论,都将茶的品性上升到君子的人格高度。茶的一生,就是求清白的一生。东坡总结出了自己的茶志趣,就是谋求一种茶里的清欢。如今,人们只要一提到茶道中的“清”字,对应的就是清白、清廉、清尚,足见苏东坡的茶志趣对于后世的茶文化有着何其重要的影响。
茶的滋味淡泊而丰富,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杯茶呢?苏东坡的饮茶人生多么丰富多彩,他用手中的诗笔,描绘了清丽雅致的茶中趣,彰显了清白做人、清廉处世的高洁品质。穿越古今,与东坡先生对饮一盏茶,仿佛是“神游天地外”的一次精神升华,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