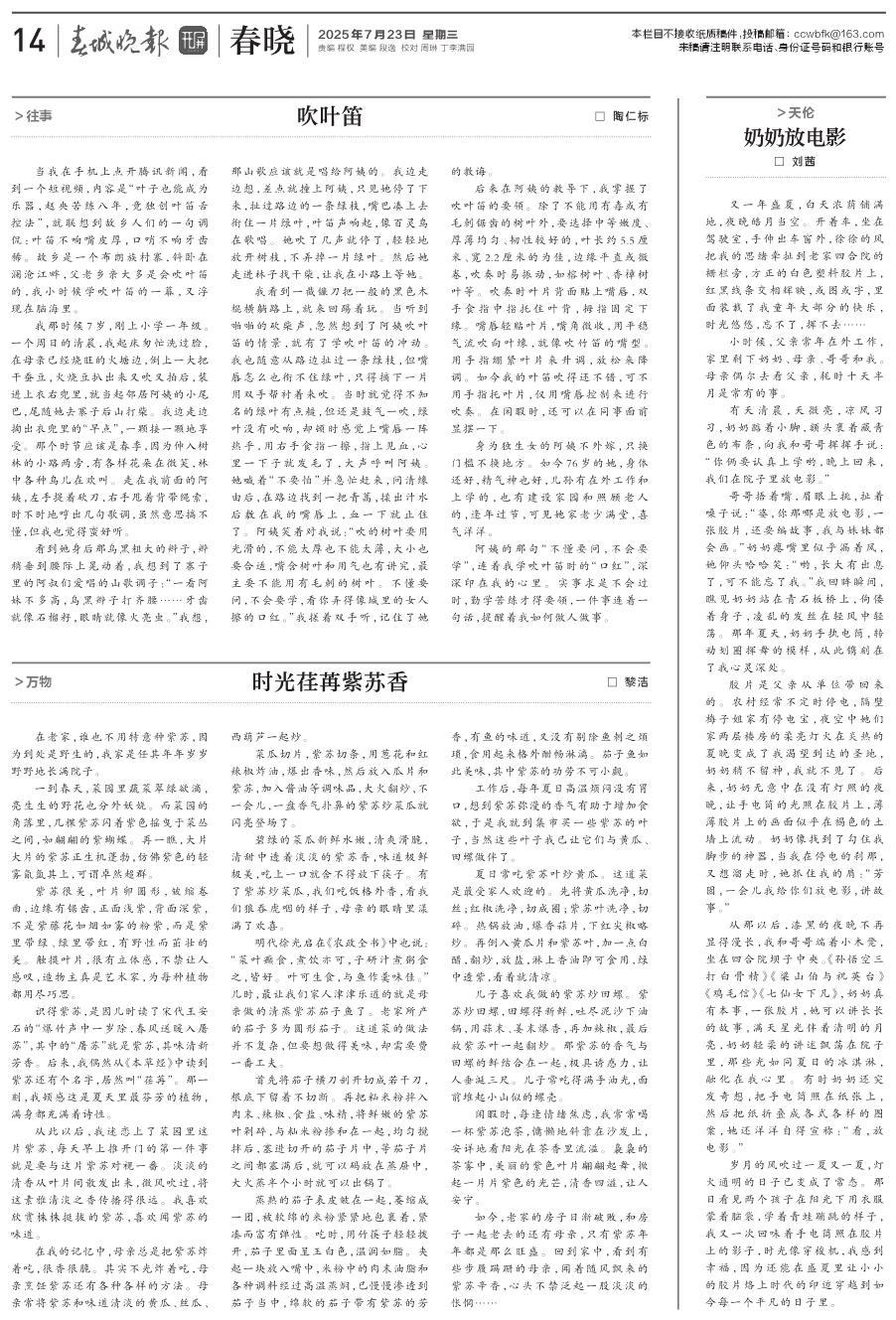□ 陶仁标
当我在手机上点开腾讯新闻,看到一个短视频,内容是“叶子也能成为乐器,赵央苦练八年,竟独创叶笛舌控法”,就联想到故乡人们的一句调侃:叶笛不响嘴皮厚,口哨不响牙齿稀。故乡是一个布朗族村寨,斜卧在澜沧江畔,父老乡亲大多是会吹叶笛的,我小时候学吹叶笛的一幕,又浮现在脑海里。
我那时候7岁,刚上小学一年级。一个周日的清晨,我起床匆忙洗过脸,在母亲已经烧旺的火塘边,倒上一大把干蚕豆,火烧豆扒出来又吹又拍后,装进上衣右兜里,就当起邻居阿姨的小尾巴,尾随她去寨子后山打柴。我边走边掏出衣兜里的“早点”,一颗接一颗地享受。那个时节应该是春季,因为伸入树林的小路两旁,有各样花朵在微笑,林中各种鸟儿在欢叫。走在我前面的阿姨,左手提着砍刀,右手甩着背带绳索,时不时地哼出几句歌调,虽然意思搞不懂,但我也觉得蛮好听。
看到她身后那乌黑粗大的辫子,辫稍垂到腰际上晃动着,我想到了寨子里的阿叔们爱唱的山歌调子:“一看阿妹不多高,乌黑辫子打齐腰……牙齿就像石榴籽,眼睛就像火亮虫。”我想,那山歌应该就是唱给阿姨的。我边走边想,差点就撞上阿姨,只见她停了下来,扯过路边的一条绿枝,嘴巴凑上去衔住一片绿叶,叶笛声响起,像百灵鸟在歌唱。她吹了几声就停了,轻轻地放开树枝,不弄掉一片绿叶。然后她走进林子找干柴,让我在小路上等她。
我看到一截镰刀把一般的黑色木棍横躺路上,就来回踢着玩。当听到啪啪的砍柴声,忽然想到了阿姨吹叶笛的情景,就有了学吹叶笛的冲动。我也随意从路边扯过一条绿枝,但嘴唇怎么也衔不住绿叶,只得摘下一片用双手帮衬着来吹。当时就觉得不知名的绿叶有点糙,但还是鼓气一吹,绿叶没有吹响,却顿时感觉上嘴唇一阵热乎,用右手食指一擦,指上见血,心里一下子就发毛了,大声呼叫阿姨。她喊着“不要怕”并急忙赶来,问清缘由后,在路边找到一把青蒿,揉出汁水后敷在我的嘴唇上,血一下就止住了。阿姨笑着对我说:“吹的树叶要用光滑的,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大小也要合适,嘴含树叶和用气也有讲究,最主要不能用有毛刺的树叶。不懂要问,不会要学,看你弄得像城里的女人擦的口红。”我搓着双手听,记住了她的教诲。
后来在阿姨的教导下,我掌握了吹叶笛的要领。除了不能用有毒或有毛刺锯齿的树叶外,要选择中等嫩度、厚薄均匀、韧性较好的,叶长约5.5厘米、宽2.2厘米的为佳,边缘平直或微卷,吹奏时易振动,如榕树叶、香樟树叶等。吹奏时叶片背面贴上嘴唇,双手食指中指托住叶背,拇指固定下缘。嘴唇轻贴叶片,嘴角微收,用平稳气流吹向叶缘,就像吹竹笛的嘴型。用手指绷紧叶片来升调,放松来降调。如今我的叶笛吹得还不错,可不用手指托叶片,仅用嘴唇控制来进行吹奏。在闲暇时,还可以在同事面前显摆一下。
身为独生女的阿姨不外嫁,只换门槛不换地方。如今76岁的她,身体还好,精气神也好,儿孙有在外工作和上学的,也有建设家园和照顾老人的,逢年过节,可见她家老少满堂,喜气洋洋。
阿姨的那句“不懂要问,不会要学”,连着我学吹叶笛时的“口红”,深深印在我的心里。实事求是不会过时,勤学苦练才得要领,一件事连着一句话,提醒着我如何做人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