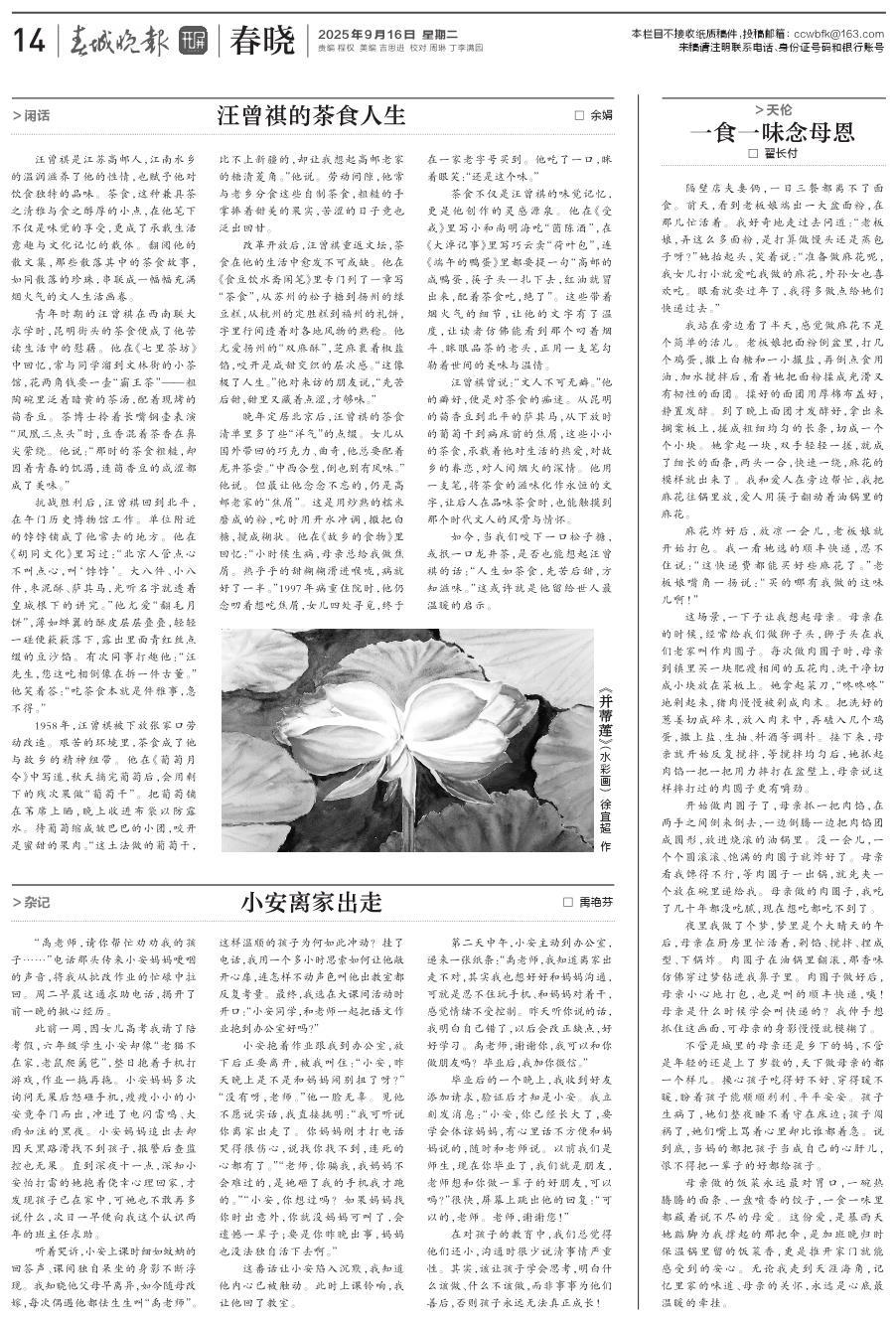□ 余娟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江南水乡的温润滋养了他的性情,也赋予他对饮食独特的品味。茶食,这种兼具茶之清雅与食之醇厚的小点,在他笔下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成了承载生活意趣与文化记忆的载体。翻阅他的散文集,那些散落其中的茶食故事,如同散落的珍珠,串联成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文人生活画卷。
青年时期的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昆明街头的茶食便成了他苦读生活中的慰藉。他在《七里茶坊》中回忆,常与同学溜到文林街的小茶馆,花两角钱要一壶“霸王茶”——粗陶碗里泛着暗黄的茶汤,配着现烤的茴香豆。茶博士拎着长嘴铜壶表演“凤凰三点头”时,豆香混着茶香在鼻尖萦绕。他说:“那时的茶食粗糙,却因着青春的饥渴,连茴香豆的咸涩都成了美味。”
抗战胜利后,汪曾祺回到北平,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单位附近的饽饽铺成了他常去的地方。他在《胡同文化》里写过:“北京人管点心不叫点心,叫‘饽饽’。大八件、小八件,枣泥酥、萨其马,光听名字就透着皇城根下的讲究。”他尤爱“翻毛月饼”,薄如蝉翼的酥皮层层叠叠,轻轻一碰便簌簌落下,露出里面青红丝点缀的豆沙馅。有次同事打趣他:“汪先生,您这吃相倒像在拆一件古董。”他笑着答:“吃茶食本就是件雅事,急不得。”
1958年,汪曾祺被下放张家口劳动改造。艰苦的环境里,茶食成了他与故乡的精神纽带。他在《葡萄月令》中写道,秋天摘完葡萄后,会用剩下的残次果做“葡萄干”。把葡萄铺在苇席上晒,晚上收进布袋以防露水。待葡萄缩成皱巴巴的小团,咬开是蜜甜的果肉。“这土法做的葡萄干,比不上新疆的,却让我想起高邮老家的糖渍菱角。”他说。劳动间隙,他常与老乡分食这些自制茶食,粗糙的手掌捧着甜美的果实,苦涩的日子竟也泛出回甘。
改革开放后,汪曾祺重返文坛,茶食在他的生活中愈发不可或缺。他在《食豆饮水斋闲笔》里专门列了一章写“茶食”,从苏州的松子糖到扬州的绿豆糕,从杭州的定胜糕到福州的礼饼,字里行间透着对各地风物的熟稔。他尤爱扬州的“双麻酥”,芝麻裹着椒盐馅,咬开是咸甜交织的层次感。“这像极了人生。”他对来访的朋友说,“先苦后甜,甜里又藏着点涩,才够味。”
晚年定居北京后,汪曾祺的茶食清单里多了些“洋气”的点缀。女儿从国外带回的巧克力、曲奇,他总要配着龙井茶尝。“中西合璧,倒也别有风味。”他说。但最让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高邮老家的“焦屑”。这是用炒熟的糯米磨成的粉,吃时用开水冲调,撒把白糖,搅成糊状。他在《故乡的食物》里回忆:“小时候生病,母亲总给我做焦屑。热乎乎的甜糊糊滑进喉咙,病就好了一半。”1997年病重住院时,他仍念叨着想吃焦屑,女儿四处寻觅,终于在一家老字号买到。他吃了一口,眯着眼笑:“还是这个味。”
茶食不仅是汪曾祺的味觉记忆,更是他创作的灵感源泉。他在《受戒》里写小和尚明海吃“茵陈酒”,在《大淖记事》里写巧云卖“荷叶包”,连《端午的鸭蛋》里都要提一句“高邮的咸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红油就冒出来,配着茶食吃,绝了”。这些带着烟火气的细节,让他的文字有了温度,让读者仿佛能看到那个叼着烟斗、眯眼品茶的老头,正用一支笔勾勒着世间的美味与温情。
汪曾祺曾说:“文人不可无癖。”他的癖好,便是对茶食的痴迷。从昆明的茴香豆到北平的萨其马,从下放时的葡萄干到病床前的焦屑,这些小小的茶食,承载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故乡的眷恋,对人间烟火的深情。他用一支笔,将茶食的滋味化作永恒的文字,让后人在品味茶食时,也能触摸到那个时代文人的风骨与情怀。
如今,当我们咬下一口松子糖,或抿一口龙井茶,是否也能想起汪曾祺的话:“人生如茶食,先苦后甜,方知滋味。”这或许就是他留给世人最温暖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