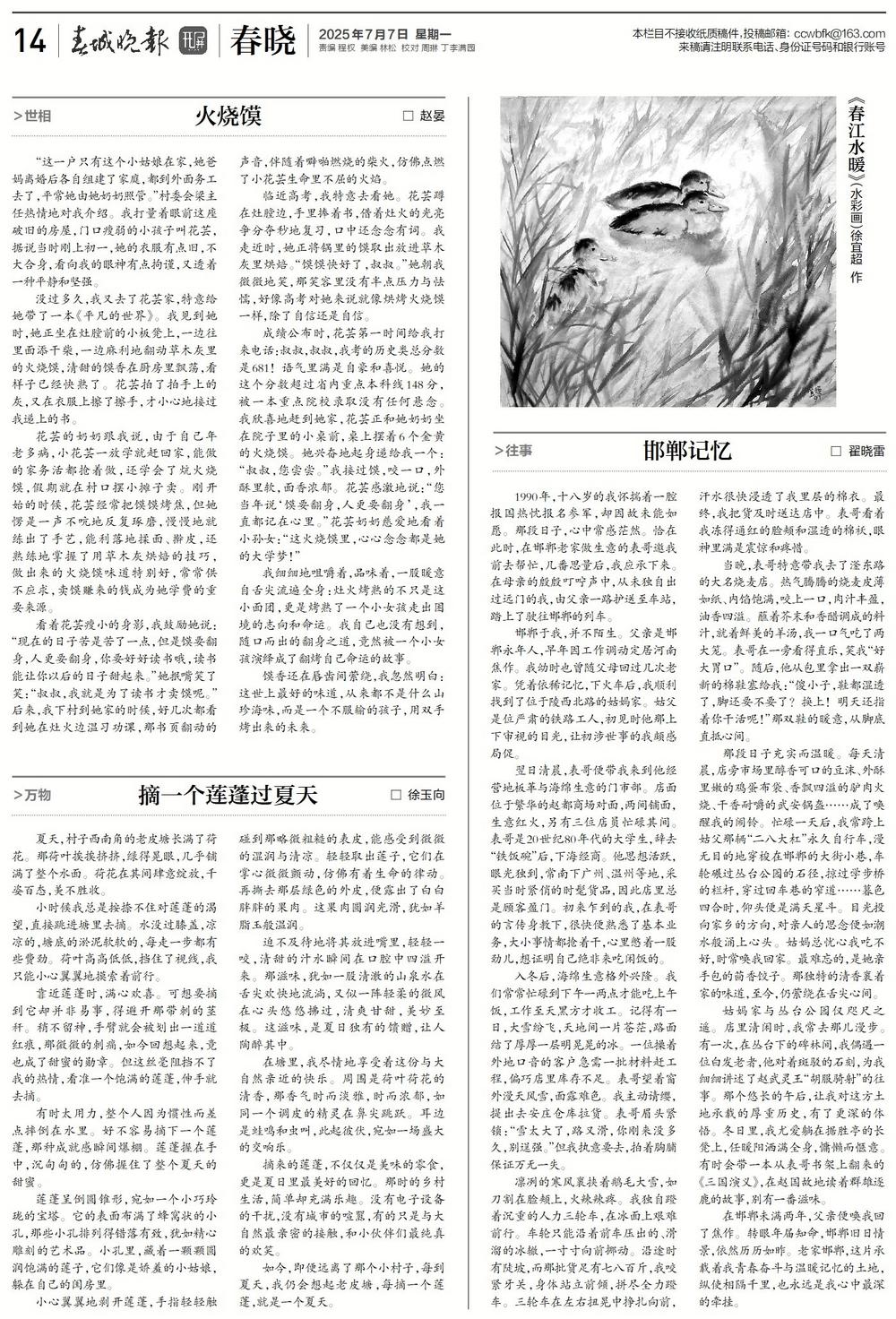□ 翟晓雷
1990年,十八岁的我怀揣着一腔报国热忱报名参军,却因故未能如愿。那段日子,心中常感茫然。恰在此时,在邯郸老家做生意的表哥邀我前去帮忙,几番思量后,我应承下来。在母亲的殷殷叮咛声中,从未独自出过远门的我,由父亲一路护送至车站,踏上了驶往邯郸的列车。
邯郸于我,并不陌生。父亲是邯郸永年人,早年因工作调动定居河南焦作。我幼时也曾随父母回过几次老家。凭着依稀记忆,下火车后,我顺利找到了位于陵西北路的姑妈家。姑父是位严肃的铁路工人,初见时他那上下审视的目光,让初涉世事的我颇感局促。
翌日清晨,表哥便带我来到他经营地板革与海绵生意的门市部。店面位于繁华的赵都商场对面,两间铺面,生意红火,另有三位店员忙碌其间。表哥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辞去“铁饭碗”后,下海经商。他思想活跃,眼光独到,常南下广州、温州等地,采买当时紧俏的时髦货品,因此店里总是顾客盈门。初来乍到的我,在表哥的言传身教下,很快便熟悉了基本业务,大小事情都抢着干,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想证明自己绝非来吃闲饭的。
入冬后,海绵生意格外兴隆。我们常常忙碌到下午一两点才能吃上午饭,工作至天黑方才收工。记得有一日,大雪纷飞,天地间一片苍茫,路面结了厚厚一层明晃晃的冰。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客户急需一批材料赶工程,偏巧店里库存不足。表哥望着窗外漫天风雪,面露难色。我主动请缨,提出去安庄仓库拉货。表哥眉头紧锁:“雪太大了,路又滑,你刚来没多久,别逞强。”但我执意要去,拍着胸脯保证万无一失。
凛冽的寒风裹挟着鹅毛大雪,如刀割在脸颊上,火辣辣疼。我独自蹬着沉重的人力三轮车,在冰面上艰难前行。车轮只能沿着前车压出的、滑溜的冰辙,一寸寸向前挪动。沿途时有陡坡,而那批货足有七八百斤,我咬紧牙关,身体站立前倾,拼尽全力蹬车。三轮车在左右扭晃中挣扎向前,汗水很快浸透了我里层的棉衣。最终,我把货及时送达店中。表哥看着我冻得通红的脸颊和湿透的棉袄,眼神里满是震惊和疼惜。
当晚,表哥特意带我去了滏东路的大名烧麦店。热气腾腾的烧麦皮薄如纸、内馅饱满,咬上一口,肉汁丰盈,油香四溢。蘸着芥末和香醋调成的料汁,就着鲜美的羊汤,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笼。表哥在一旁看得直乐,笑我“好大胃口”。随后,他从包里拿出一双崭新的棉鞋塞给我:“傻小子,鞋都湿透了,脚还要不要了?换上!明天还指着你干活呢!”那双鞋的暖意,从脚底直抵心间。
那段日子充实而温暖。每天清晨,店旁市场里醇香可口的豆沫、外酥里嫩的鸡蛋布袋、香飘四溢的驴肉火烧、干香耐嚼的武安锅盔……成了唤醒我的闹铃。忙碌一天后,我常跨上姑父那辆“二八大杠”永久自行车,漫无目的地穿梭在邯郸的大街小巷,车轮碾过丛台公园的石径,掠过学步桥的栏杆,穿过回车巷的窄道……暮色四合时,仰头便是满天星斗。目光投向家乡的方向,对亲人的思念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姑妈总忧心我吃不好,时常唤我回家。最难忘的,是她亲手包的茴香饺子。那独特的清香裹着家的味道,至今,仍萦绕在舌尖心间。
姑妈家与丛台公园仅咫尺之遥。店里清闲时,我常去那儿漫步。有一次,在丛台下的碑林间,我偶遇一位白发老者,他对着斑驳的石刻,为我细细讲述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往事。那个悠长的午后,让我对这方土地承载的厚重历史,有了更深的体悟。冬日里,我尤爱躺在据胜亭的长凳上,任暖阳洒满全身,慵懒而惬意。有时会带一本从表哥书架上翻来的《三国演义》,在赵国故地读着群雄逐鹿的故事,别有一番滋味。
在邯郸未满两年,父亲便唤我回了焦作。转眼年届知命,邯郸旧日情景,依然历历如昨。老家邯郸,这片承载着我青春奋斗与温暖记忆的土地,纵使相隔千里,也永远是我心中最深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