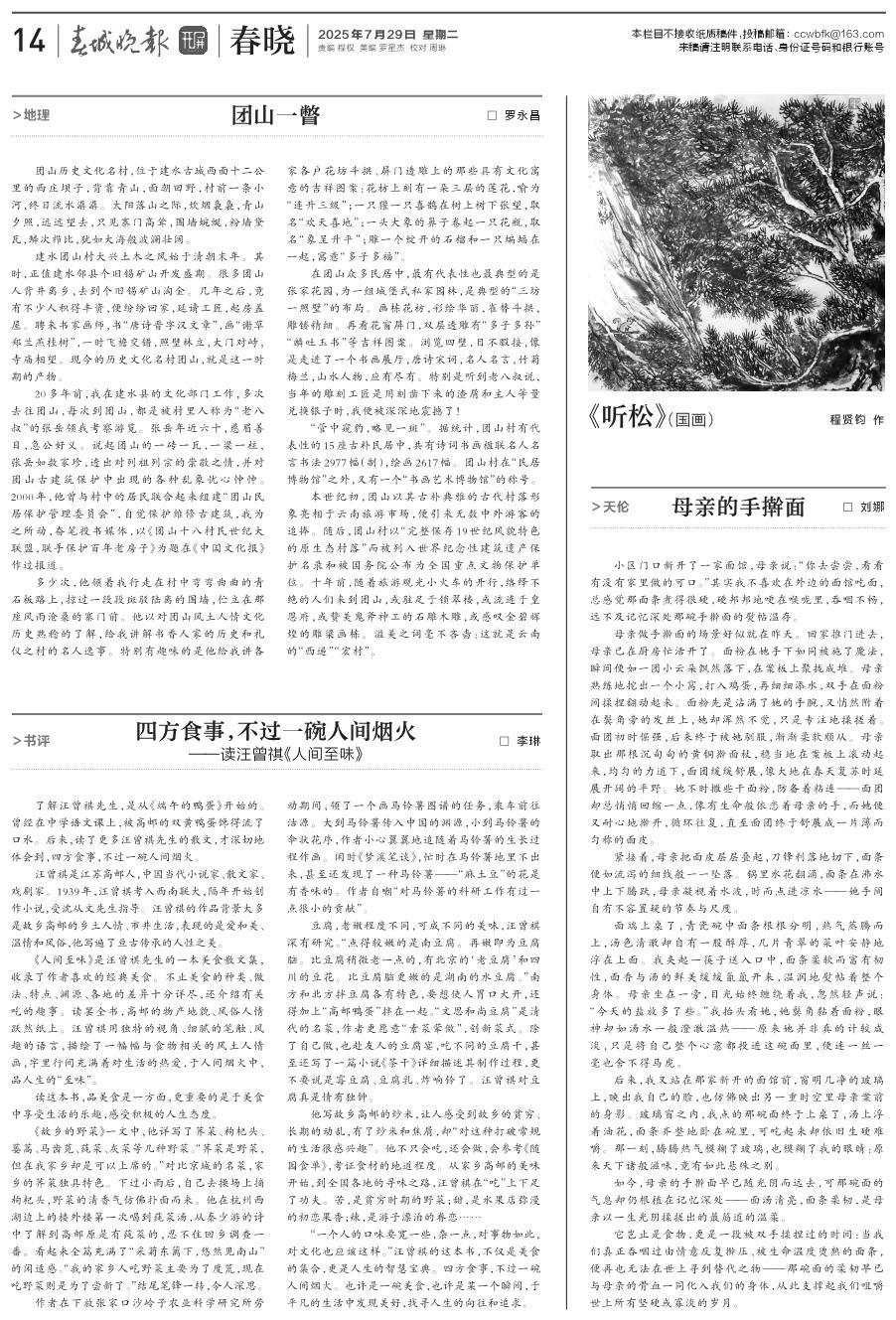□ 刘娜
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面馆,母亲说:“你去尝尝,看看有没有家里做的可口。”其实我不喜欢在外边的面馆吃面,总感觉那面条煮得很硬,硬邦邦地哽在喉咙里,吞咽不畅,远不及记忆深处那碗手擀面的熨帖温存。
母亲做手擀面的场景好似就在昨天。回家推门进去,母亲已在厨房忙活开了。面粉在她手下如同被施了魔法,瞬间便如一团小云朵飘然落下,在案板上聚拢成堆。母亲熟练地挖出一个小窝,打入鸡蛋,再细细添水,双手在面粉间揉捏翻动起来。面粉先是沾满了她的手腕,又悄然附着在鬓角旁的发丝上,她却浑然不觉,只是专注地揉搓着。面团初时倔强,后来终于被她驯服,渐渐柔软顺从。母亲取出那根沉甸甸的黄铜擀面杖,稳当地在案板上滚动起来,均匀的力道下,面团缓缓舒展,像大地在春天复苏时延展开阔的平野。她不时撒些干面粉,防备着粘连——面团却总悄悄回缩一点,像有生命般依恋着母亲的手,而她便又耐心地擀开,循环往复,直至面团终于舒展成一片薄而匀称的面皮。
紧接着,母亲把面皮层层叠起,刀锋利落地切下,面条便如流泻的细线般一一坠落。锅里水花翻涌,面条在沸水中上下腾跃,母亲凝视着水波,时而点进凉水——她手间自有不容置疑的节奏与尺度。
面端上桌了,青瓷碗中面条根根分明,热气蒸腾而上,汤色清澈却自有一股醇厚,几片青翠的菜叶安静地浮在上面。我夹起一筷子送入口中,面条柔软而富有韧性,面香与汤的鲜美缓缓氤氲开来,温润地熨帖着整个身体。母亲坐在一旁,目光始终缠绕着我,忽然轻声说:“今天的盐放多了些。”我抬头看她,她鬓角黏着面粉,眼神却如汤水一般澄澈温热——原来她并非真的计较咸淡,只是将自己整个心意都投进这碗面里,便连一丝一毫也舍不得马虎。
后来,我又站在那家新开的面馆前,窗明几净的玻璃上,映出我自己的脸,也仿佛映出另一重时空里母亲案前的身影。玻璃窗之内,我点的那碗面终于上桌了,汤上浮着油花,面条齐整地卧在碗里,可吃起来却依旧生硬难嚼。那一刻,腾腾热气模糊了玻璃,也模糊了我的眼睛:原来天下诸般滋味,竟有如此悬殊之别。
如今,母亲的手擀面早已随光阴而远去,可那碗面的气息却仍根植在记忆深处——面汤清亮,面条柔韧,是母亲以一生光阴揉搓出的最筋道的温柔。
它岂止是食物,更是一段被双手揉捏过的时间:当我们真正吞咽过由情意反复擀压、被生命温度烫熟的面条,便再也无法在世上寻到替代之物——那碗面的柔韧早已与母亲的骨血一同化入我们的身体,从此支撑起我们咀嚼世上所有坚硬或寡淡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