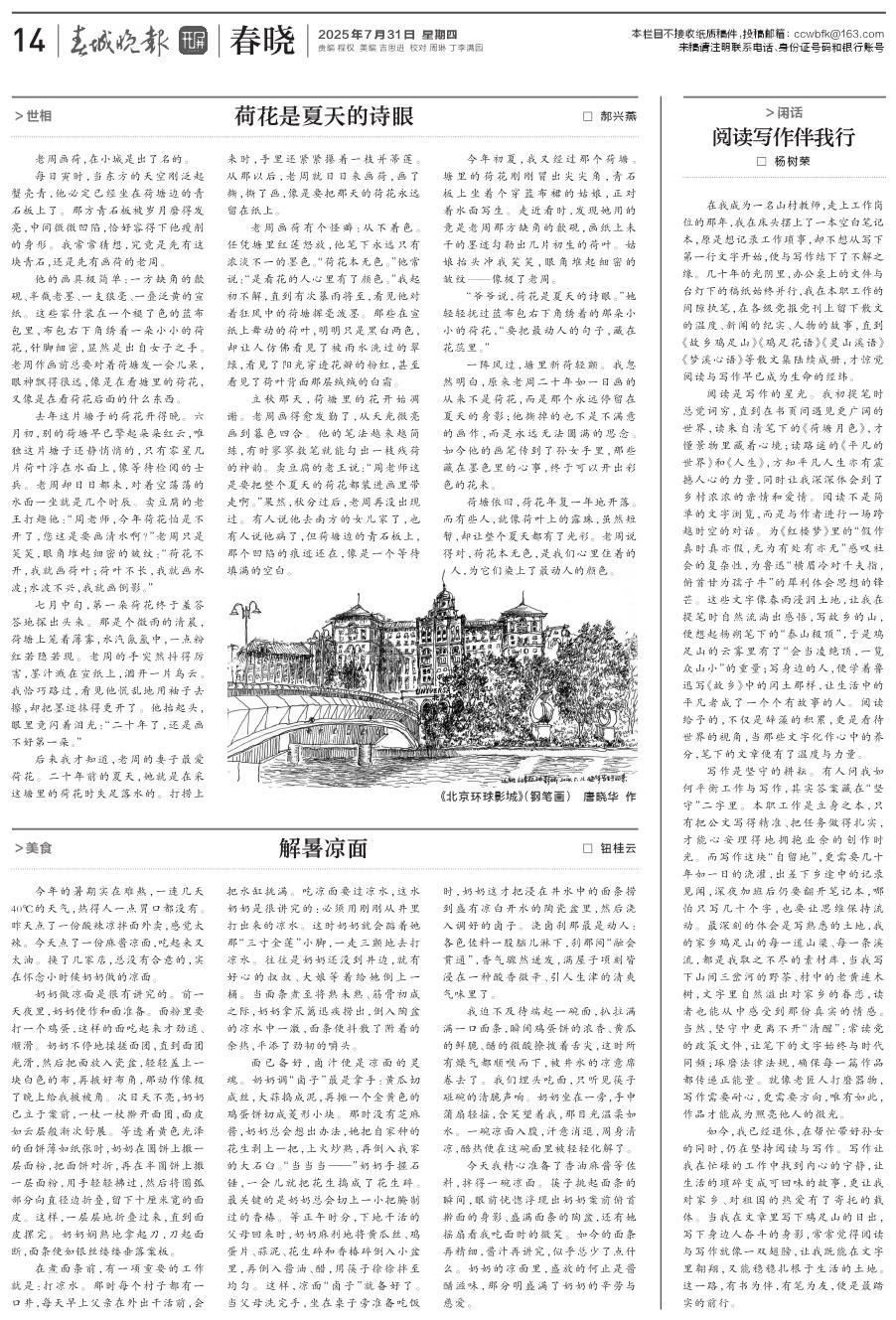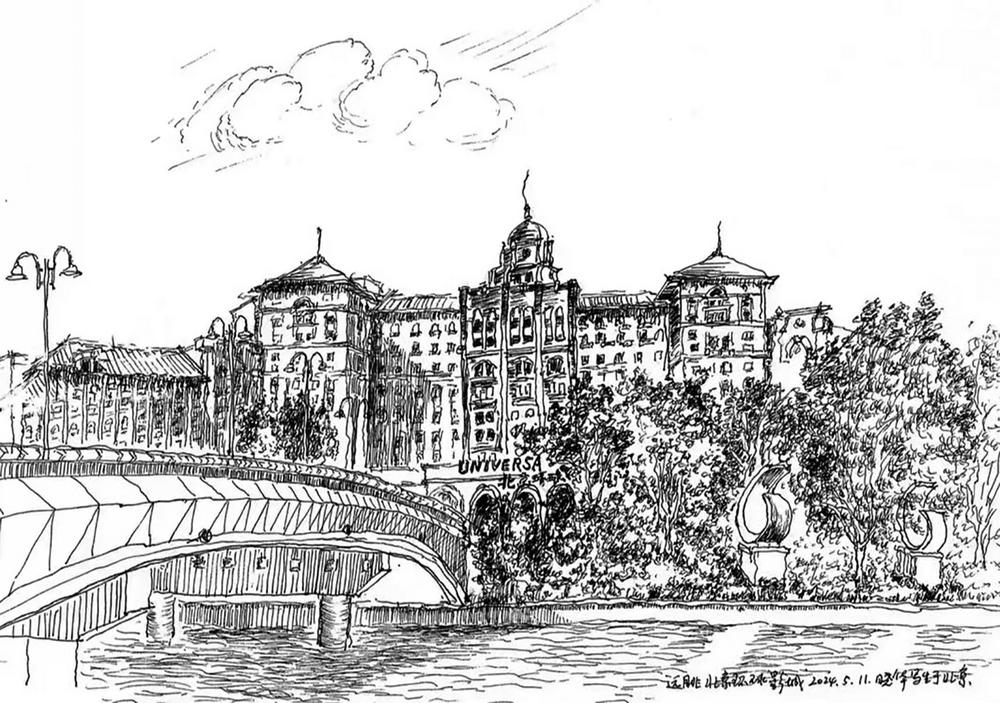□ 郝兴燕
老周画荷,在小城是出了名的。
每日寅时,当东方的天空刚泛起蟹壳青,他必定已经坐在荷塘边的青石板上了。那方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中间微微凹陷,恰好容得下他瘦削的身形。我常常猜想,究竟是先有这块青石,还是先有画荷的老周。
他的画具极简单:一方缺角的歙砚、半截老墨、一支狼毫、一叠泛黄的宣纸。这些家什装在一个褪了色的蓝布包里,布包右下角绣着一朵小小的荷花,针脚细密,显然是出自女子之手。老周作画前总要对着荷塘发一会儿呆,眼神飘得很远,像是在看塘里的荷花,又像是在看荷花后面的什么东西。
去年这片塘子的荷花开得晚。六月初,别的荷塘早已擎起朵朵红云,唯独这片塘子还静悄悄的,只有零星几片荷叶浮在水面上,像等待检阅的士兵。老周却日日都来,对着空荡荡的水面一坐就是几个时辰。卖豆腐的老王打趣他:“周老师,今年荷花怕是不开了,您这是要画清水啊?”老周只是笑笑,眼角堆起细密的皱纹:“荷花不开,我就画荷叶;荷叶不长,我就画水波;水波不兴,我就画倒影。”
七月中旬,第一朵荷花终于羞答答地探出头来。那是个微雨的清晨,荷塘上笼着薄雾,水汽氤氲中,一点粉红若隐若现。老周的手突然抖得厉害,墨汁溅在宣纸上,洇开一片乌云。我恰巧路过,看见他慌乱地用袖子去擦,却把墨迹抹得更开了。他抬起头,眼里竟闪着泪光:“二十年了,还是画不好第一朵。”
后来我才知道,老周的妻子最爱荷花。二十年前的夏天,她就是在采这塘里的荷花时失足落水的。打捞上来时,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枝并蒂莲。从那以后,老周就日日来画荷,画了撕,撕了画,像是要把那天的荷花永远留在纸上。
老周画荷有个怪癖:从不着色。任凭塘里红莲怒放,他笔下永远只有浓淡不一的墨色。“荷花本无色。”他常说:“是看花的人心里有了颜色。”我起初不解,直到有次暴雨将至,看见他对着狂风中的荷塘挥毫泼墨。那些在宣纸上舞动的荷叶,明明只是黑白两色,却让人仿佛看见了被雨水洗过的翠绿,看见了阳光穿透花瓣的粉红,甚至看见了荷叶背面那层绒绒的白霜。
立秋那天,荷塘里的花开始凋谢。老周画得愈发勤了,从天光微亮画到暮色四合。他的笔法越来越简练,有时寥寥数笔就能勾出一枝残荷的神韵。卖豆腐的老王说:“周老师这是要把整个夏天的荷花都装进画里带走啊。”果然,秋分过后,老周再没出现过。有人说他去南方的女儿家了,也有人说他病了,但荷塘边的青石板上,那个凹陷的痕迹还在,像是一个等待填满的空白。
今年初夏,我又经过那个荷塘。塘里的荷花刚刚冒出尖尖角,青石板上坐着个穿蓝布裙的姑娘,正对着水面写生。走近看时,发现她用的竟是老周那方缺角的歙砚,画纸上未干的墨迹勾勒出几片初生的荷叶。姑娘抬头冲我笑笑,眼角堆起细密的皱纹——像极了老周。
“爷爷说,荷花是夏天的诗眼。”她轻轻抚过蓝布包右下角绣着的那朵小小的荷花,“要把最动人的句子,藏在花蕊里。”
一阵风过,塘里新荷轻颤。我忽然明白,原来老周二十年如一日画的从来不是荷花,而是那个永远停留在夏天的身影;他撕掉的也不是不满意的画作,而是永远无法圆满的思念。如今他的画笔传到了孙女手里,那些藏在墨色里的心事,终于可以开出彩色的花来。
荷塘依旧,荷花年复一年地开落。而有些人,就像荷叶上的露珠,虽然短暂,却让整个夏天都有了光彩。老周说得对,荷花本无色,是我们心里住着的人,为它们染上了最动人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