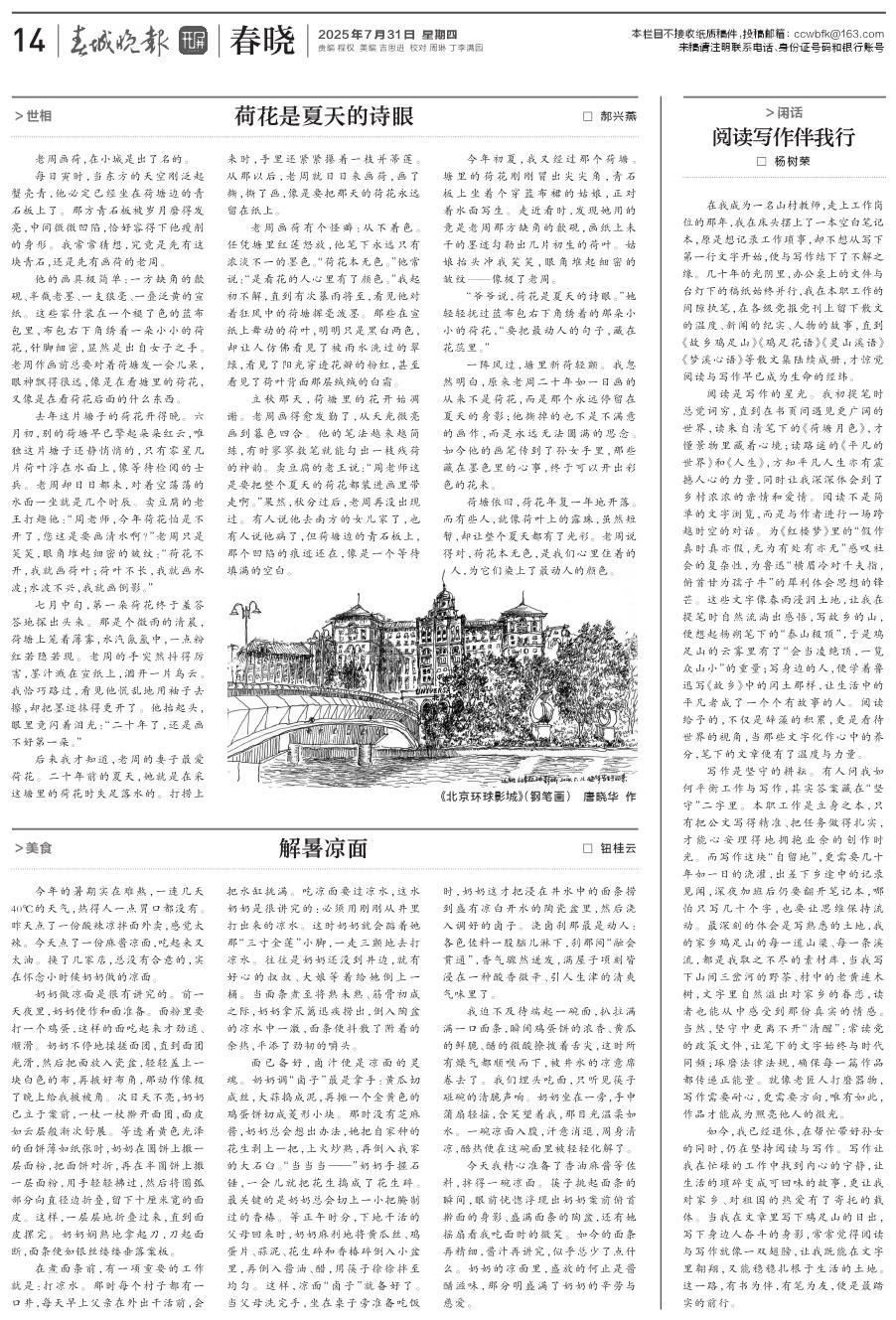□ 钮桂云
今年的暑期实在难熬,一连几天40℃的天气,热得人一点胃口都没有。昨天点了一份酸辣凉拌面外卖,感觉太辣。今天点了一份麻酱凉面,吃起来又太油。换了几家店,总没有合意的,实在怀念小时候奶奶做的凉面。
奶奶做凉面是很有讲究的。前一天夜里,奶奶便作和面准备。面粉里要打一个鸡蛋,这样的面吃起来才劲道、顺滑。奶奶不停地揉搓面团,直到面团光滑,然后把面放入瓷盆,轻轻盖上一块白色的布,再掖好布角,那动作像极了晚上给我掖被角。次日天不亮,奶奶已立于案前,一杖一杖擀开面团,面皮如云层般渐次舒展。等透着黄色光泽的面饼薄如纸张时,奶奶在圆饼上撒一层面粉,把面饼对折,再在半圆饼上撒一层面粉,用手轻轻拂过,然后将圆弧部分向直径边折叠,留下十厘米宽的面皮。这样,一层层地折叠过来,直到面皮摞完。奶奶娴熟地拿起刀,刀起面断,面条便如银丝缕缕垂落案板。
在煮面条前,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打凉水。那时每个村子都有一口井,每天早上父亲在外出干活前,会把水缸挑满。吃凉面要过凉水,这水奶奶是很讲究的:必须用刚刚从井里打出来的凉水。这时奶奶就会踮着她那“三寸金莲”小脚,一走三颤地去打凉水。往往是奶奶还没到井边,就有好心的叔叔、大娘等着给她倒上一桶。当面条煮至将熟未熟、筋骨初成之际,奶奶拿笊篱迅疾捞出,倒入陶盆的凉水中一激,面条便抖散了附着的余热,平添了劲韧的嚼头。
面已备好,卤汁便是凉面的灵魂。奶奶调“卤子”最是拿手:黄瓜切成丝,大蒜捣成泥,再摊一个金黄色的鸡蛋饼切成菱形小块。那时没有芝麻酱,奶奶总会想出办法,她把自家种的花生剥上一把,上火炒熟,再倒入我家的大石臼。“当当当——”奶奶手握石锤,一会儿就把花生捣成了花生碎。最关键的是奶奶总会切上一小把腌制过的香椿。等正午时分,下地干活的父母回来时,奶奶麻利地将黄瓜丝、鸡蛋片、蒜泥、花生碎和香椿碎倒入小盆里,再倒入酱油、醋,用筷子徐徐拌至均匀。这样,凉面“卤子”就备好了。当父母洗完手,坐在桌子旁准备吃饭时,奶奶这才把浸在井水中的面条捞到盛有凉白开水的陶瓷盆里,然后浇入调好的卤子。浇卤刹那最是动人:各色佐料一股脑儿淋下,刹那间“融会贯通”,香气骤然迸发,满屋子顷刻皆浸在一种酸香微辛、引人生津的清爽气味里了。
我迫不及待端起一碗面,扒拉满满一口面条,瞬间鸡蛋饼的浓香、黄瓜的鲜脆、醋的微酸撩拨着舌尖,这时所有燥气都顺喉而下,被井水的凉意席卷去了。我们埋头吃面,只听见筷子碰碗的清脆声响。奶奶坐在一旁,手中蒲扇轻摇,含笑望着我,那目光温柔如水。一碗凉面入腹,汗意消退,周身清凉,酷热便在这碗面里被轻轻化解了。
今天我精心准备了香油麻酱等佐料,拌得一碗凉面。筷子挑起面条的瞬间,眼前恍惚浮现出奶奶案前俯首擀面的身影、盛满面条的陶盆,还有她摇扇看我吃面时的微笑。如今的面条再精细,酱汁再讲究,似乎总少了点什么。奶奶的凉面里,盛放的何止是酱醋滋味,那分明盛满了奶奶的辛劳与慈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