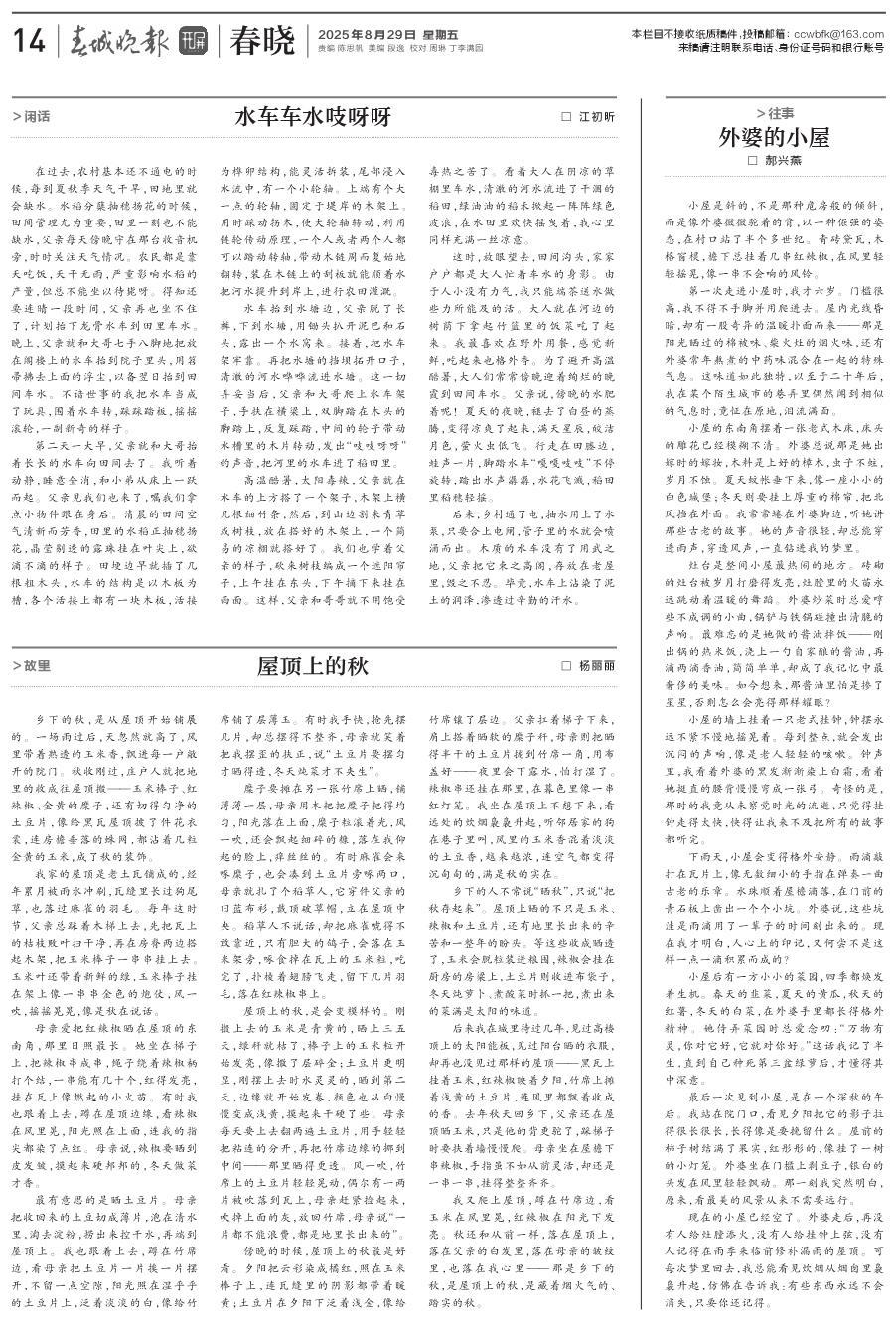□ 郝兴燕
小屋是斜的,不是那种危房般的倾斜,而是像外婆微微驼着的背,以一种倔强的姿态,在村口站了半个多世纪。青砖黛瓦,木格窗棂,檐下总挂着几串红辣椒,在风里轻轻摇晃,像一串不会响的风铃。
第一次走进小屋时,我才六岁。门槛很高,我不得不手脚并用爬进去。屋内光线昏暗,却有一股奇异的温暖扑面而来——那是阳光晒过的棉被味、柴火灶的烟火味,还有外婆常年熬煮的中药味混合在一起的特殊气息。这味道如此独特,以至于二十年后,我在某个陌生城市的巷弄里偶然闻到相似的气息时,竟怔在原地,泪流满面。
小屋的东南角摆着一张老式木床,床头的雕花已经模糊不清。外婆总说那是她出嫁时的嫁妆,木料是上好的樟木,虫子不蛀,岁月不蚀。夏天蚊帐垂下来,像一座小小的白色城堡;冬天则要挂上厚重的棉帘,把北风挡在外面。我常常蜷在外婆脚边,听她讲那些古老的故事。她的声音很轻,却总能穿透雨声,穿透风声,一直钻进我的梦里。
灶台是整间小屋最热闹的地方。砖砌的灶台被岁月打磨得发亮,灶膛里的火苗永远跳动着温暖的舞蹈。外婆炒菜时总爱哼些不成调的小曲,锅铲与铁锅碰撞出清脆的声响。最难忘的是她做的酱油拌饭——刚出锅的热米饭,浇上一勺自家酿的酱油,再滴两滴香油,简简单单,却成了我记忆中最奢侈的美味。如今想来,那酱油里怕是掺了星星,否则怎么会亮得那样耀眼?
小屋的墙上挂着一只老式挂钟,钟摆永远不紧不慢地摇晃着。每到整点,就会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是老人轻轻的咳嗽。钟声里,我看着外婆的黑发渐渐染上白霜,看着她挺直的腰背慢慢弯成一张弓。奇怪的是,那时的我竟从未察觉时光的流逝,只觉得挂钟走得太快,快得让我来不及把所有的故事都听完。
下雨天,小屋会变得格外安静。雨滴敲打在瓦片上,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弹奏一曲古老的乐章。水珠顺着屋檐滴落,在门前的青石板上凿出一个个小坑。外婆说,这些坑洼是雨滴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刻出来的。现在我才明白,人心上的印记,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
小屋后有一方小小的菜园,四季都焕发着生机。春天的韭菜,夏天的黄瓜,秋天的红薯,冬天的白菜,在外婆手里都长得格外精神。她侍弄菜园时总爱念叨:“万物有灵,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这话我记了半生,直到自己种死第三盆绿萝后,才懂得其中深意。
最后一次见到小屋,是在一个深秋的午后。我站在院门口,看见夕阳把它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得像是要挽留什么。屋前的柿子树结满了果实,红彤彤的,像挂了一树的小灯笼。外婆坐在门槛上剥豆子,银白的头发在风里轻轻飘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原来,看最美的风景从来不需要远行。
现在的小屋已经空了。外婆走后,再没有人给灶膛添火,没有人给挂钟上弦,没有人记得在雨季来临前修补漏雨的屋顶。可每次梦里回去,我总能看见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仿佛在告诉我: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只要你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