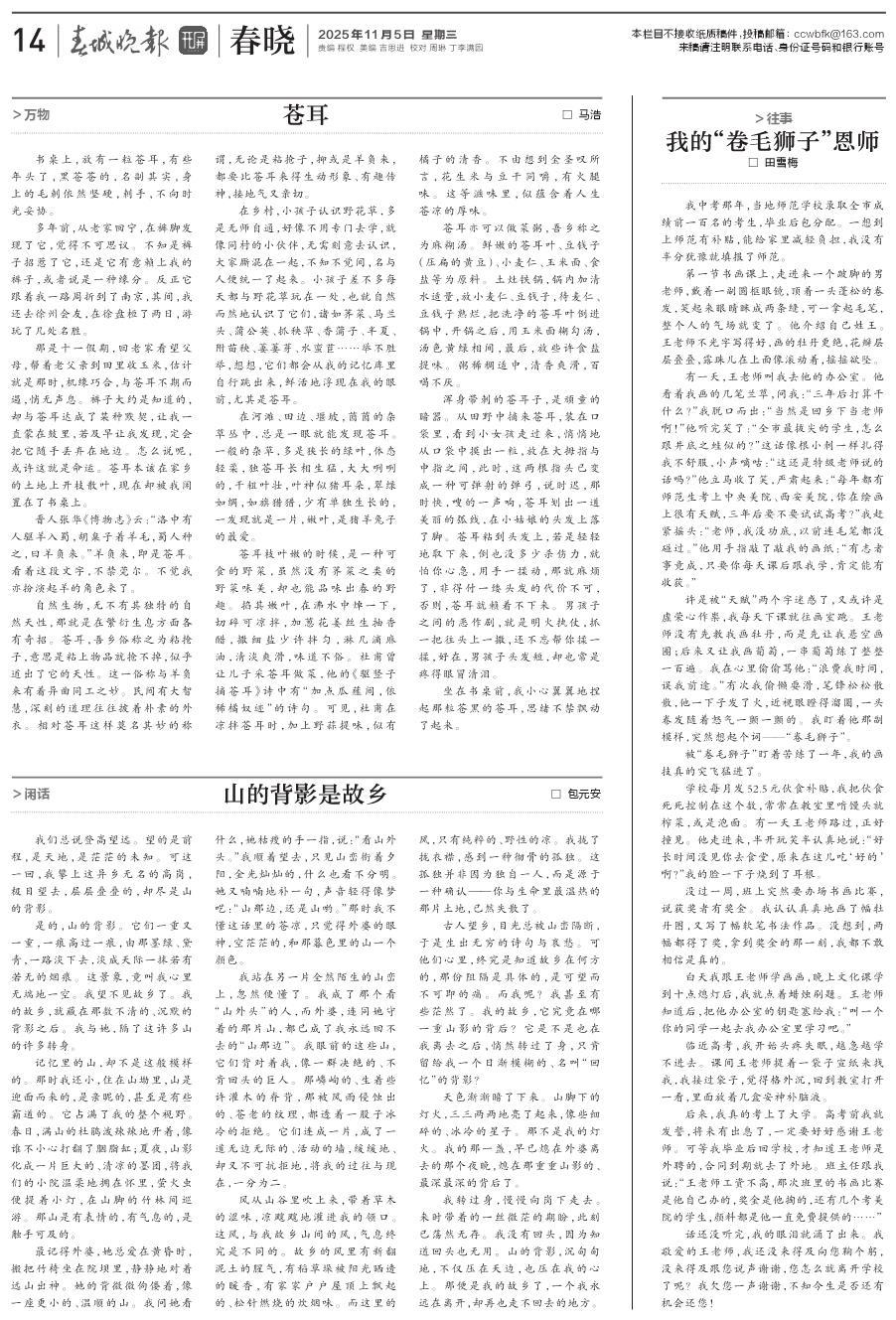□ 马浩
书桌上,放有一粒苍耳,有些年头了,黑苍苍的,名副其实,身上的毛刺依然坚硬,刺手,不向时光妥协。
多年前,从老家回宁,在裤脚发现了它,觉得不可思议。不知是裤子招惹了它,还是它有意赖上我的裤子,或者说是一种缘分。反正它跟着我一路周折到了南京,其间,我还去徐州会友,在徐盘桓了两日,游玩了几处名胜。
那是十一假期,回老家看望父母,帮着老父亲到田里收玉米,估计就是那时,机缘巧合,与苍耳不期而遇,悄无声息。裤子大约是知道的,却与苍耳达成了某种默契,让我一直蒙在鼓里,若及早让我发现,定会把它随手丢弃在地边。怎么说呢,或许这就是命运。苍耳本该在家乡的土地上开枝散叶,现在却被我闲置在了书桌上。
晋人张华《博物志》云:“洛中有人驱羊入蜀,胡枲子着羊毛,蜀人种之,曰羊负来。”羊负来,即是苍耳。看着这段文字,不禁莞尔。不觉我亦扮演起羊的角色来了。
自然生物,无不有其独特的自然天性,那就是在繁衍生息方面各有奇招。苍耳,吾乡俗称之为粘抢子,意思是粘上物品就抢不掉,似乎道出了它的天性。这一俗称与羊负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民间有大智慧,深刻的道理往往披着朴素的外衣。相对苍耳这样莫名其妙的称谓,无论是粘抢子,抑或是羊负来,都要比苍耳来得生动形象、有趣传神,接地气又亲切。
在乡村,小孩子认识野花草,多是无师自通,好像不用专门去学,就像同村的小伙伴,无需刻意去认识,大家厮混在一起,不知不觉间,名与人便统一了起来。小孩子差不多每天都与野花草玩在一处,也就自然而然地认识了它们,诸如荠菜、马兰头、蒲公英、抓秧草、香蒲子、半夏、附苗秧、萋萋芽、水蛮苣……举不胜举,想想,它们都会从我的记忆库里自行跳出来,鲜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尤其是苍耳。
在河滩、田边、堰坡,茵茵的杂草丛中,总是一眼就能发现苍耳。一般的杂草,多是狭长的绿叶,体态轻柔,独苍耳长相生猛,大大咧咧的,干粗叶壮,叶神似猪耳朵,翠绿如绸,如旗猎猎,少有单独生长的,一发现就是一片,嫩叶,是猪羊兔子的最爱。
苍耳枝叶嫩的时候,是一种可食的野菜,虽然没有荠菜之类的野菜味美,却也能品味出春的野趣。掐其嫩叶,在沸水中焯一下,切碎可凉拌,加葱花姜丝生抽香醋,撒细盐少许拌匀,淋几滴麻油,清淡爽滑,味道不俗。杜甫曾让儿子采苍耳做菜,他的《驱竖子摘苍耳》诗中有“加点瓜薤间,依稀橘奴迹”的诗句。可见,杜甫在凉拌苍耳时,加上野蒜提味,似有橘子的清香。不由想到金圣叹所言,花生米与豆干同嚼,有火腿味。这等滋味里,似蕴含着人生苍凉的厚味。
苍耳亦可以做菜粥,吾乡称之为麻糊汤。鲜嫩的苍耳叶、豆钱子(压扁的黄豆)、小麦仁、玉米面、食盐等为原料。土灶铁锅,锅内加清水适量,放小麦仁、豆钱子,待麦仁、豆钱子熟烂,把洗净的苍耳叶倒进锅中,开锅之后,用玉米面糊勾汤,汤色黄绿相间,最后,放些许食盐提味。粥稀稠适中,清香爽滑,百喝不厌。
浑身带刺的苍耳子,是顽童的暗器。从田野中摘来苍耳,装在口袋里,看到小女孩走过来,悄悄地从口袋中摸出一粒,放在大拇指与中指之间,此时,这两根指头已变成一种可弹射的弹弓,说时迟,那时快,嗖的一声响,苍耳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在小姑娘的头发上落了脚。苍耳粘到头发上,若是轻轻地取下来,倒也没多少杀伤力,就怕你心急,用手一揉动,那就麻烦了,非得付一缕头发的代价不可,否则,苍耳就赖着不下来。男孩子之间的恶作剧,就是明火执仗,抓一把往头上一撒,还不忘帮你揉一揉,好在,男孩子头发短,却也常是疼得眼冒清泪。
坐在书桌前,我小心翼翼地捏起那粒苍黑的苍耳,思绪不禁飘动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