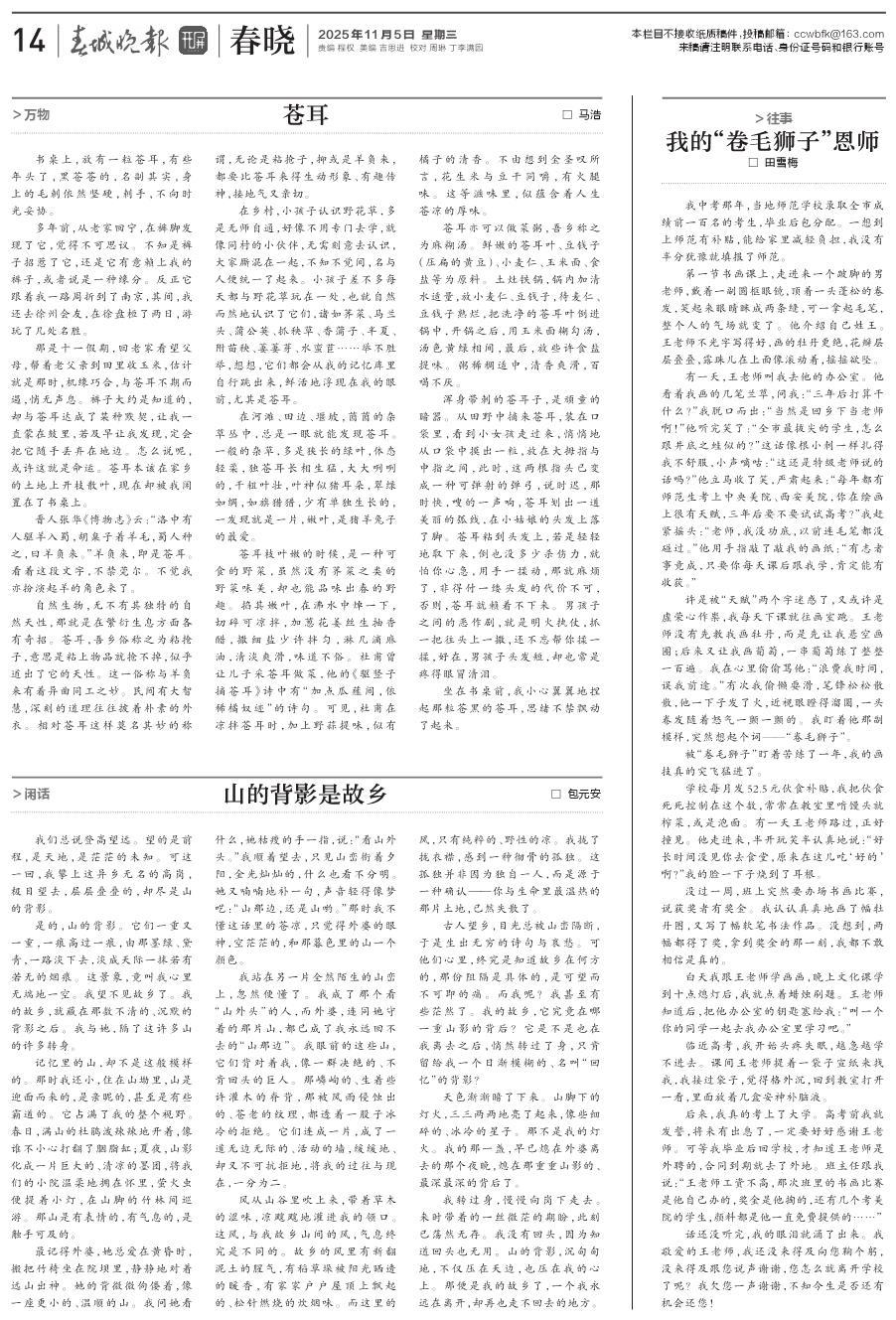□ 包元安
我们总说登高望远。望的是前程,是天地,是茫茫的未知。可这一回,我攀上这异乡无名的高岗,极目望去,层层叠叠的,却尽是山的背影。
是的,山的背影。它们一重又一重,一痕高过一痕,由那墨绿、黛青,一路淡下去,淡成天际一抹若有若无的烟痕。这景象,竟叫我心里无端地一空。我望不见故乡了。我的故乡,就藏在那数不清的、沉默的背影之后。我与她,隔了这许多山的许多转身。
记忆里的山,却不是这般模样的。那时我还小,住在山坳里,山是迎面而来的,是亲昵的,甚至是有些霸道的。它占满了我的整个视野。春日,满山的杜鹃泼辣辣地开着,像谁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缸;夏夜,山影化成一片巨大的、清凉的墨团,将我们的小院温柔地拥在怀里,萤火虫便提着小灯,在山脚的竹林间巡游。那山是有表情的,有气息的,是触手可及的。
最记得外婆,她总爱在黄昏时,搬把竹椅坐在院坝里,静静地对着远山出神。她的背微微佝偻着,像一座更小的、温顺的山。我问她看什么,她枯瘦的手一指,说:“看山外头。”我顺着望去,只见山峦衔着夕阳,金光灿灿的,什么也看不分明。她又喃喃地补一句,声音轻得像梦呓:“山那边,还是山哟。”那时我不懂这话里的苍凉,只觉得外婆的眼神,空茫茫的,和那暮色里的山一个颜色。
我站在另一片全然陌生的山峦上,忽然便懂了。我成了那个看“山外头”的人,而外婆,连同她守着的那片山,都已成了我永远回不去的“山那边”。我眼前的这些山,它们背对着我,像一群决绝的、不肯回头的巨人。那嶙峋的、生着些许灌木的脊背,那被风雨侵蚀出的、苍老的纹理,都透着一股子冰冷的拒绝。它们连成一片,成了一道无边无际的、活动的墙,缓缓地、却又不可抗拒地,将我的过往与现在,一分为二。
风从山谷里吹上来,带着草木的涩味,凉飕飕地灌进我的领口。这风,与我故乡山间的风,气息终究是不同的。故乡的风里有新翻泥土的腥气,有稻草垛被阳光晒透的暖香,有家家户户屋顶上飘起的、松针燃烧的炊烟味。而这里的风,只有纯粹的、野性的凉。我拢了拢衣襟,感到一种彻骨的孤独。这孤独并非因为独自一人,而是源于一种确认——你与生命里最温热的那片土地,已然失散了。
古人望乡,目光总被山峦隔断,于是生出无穷的诗句与哀愁。可他们心里,终究是知道故乡在何方的,那份阻隔是具体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痛。而我呢?我甚至有些茫然了。我的故乡,它究竟在哪一重山影的背后?它是不是也在我离去之后,悄然转过了身,只肯留给我一个日渐模糊的、名叫“回忆”的背影?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山脚下的灯火,三三两两地亮了起来,像些细碎的、冰冷的星子。那不是我的灯火。我的那一盏,早已熄在外婆离去的那个夜晚,熄在那重重山影的、最深最深的背后了。
我转过身,慢慢向岗下走去。来时带着的一丝微茫的期盼,此刻已荡然无存。我没有回头,因为知道回头也无用。山的背影,沉甸甸地,不仅压在天边,也压在我的心上。那便是我的故乡了,一个我永远在离开,却再也走不回去的地方。